学额制度:清代大一统的文化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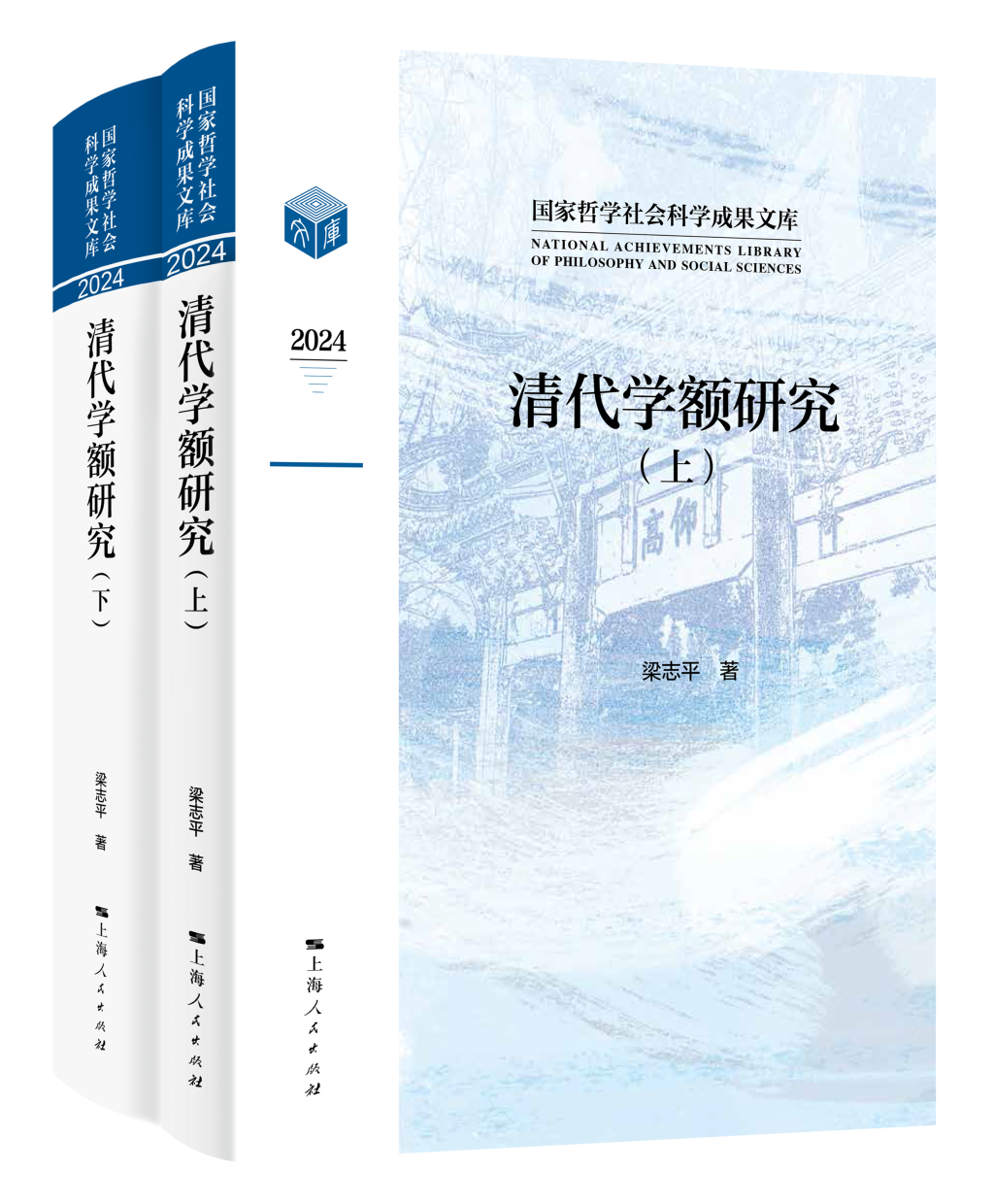
《清代学额研究》,梁志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有两个出发点完全不同的原问题。牵涉到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从西方舶来的文化地理观念,认为“文化”是相对于“自然”的人类创造,主张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各地文化面目的差异,如语言、宗教、风土民情等。这种研究的旨趣是较异同。而我国自古以来的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治教化”,它与“野蛮”“质朴”相对而论。因而按此种理路来探讨文化地域差异,就得设计一些指标,例如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的多寡,所持文化设施的丰瘠,以较其高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波及到历史地理学领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蔚然兴起。上述两个思路中,要探讨语言、宗教、风俗等现象的地域差异,牵涉到相关学科领域,难度相对较大;而对各类人物的分布加以统计分析,既没有太大的操作难度,结果又较容易引人关注,一时间风起云涌,泥沙俱下。或名之曰“人才学”,或名之曰“学术地理”,或名之“教育地理”,不一而足。
讨论人物的地理分布,一个令人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形成地域差异的原因。古人的认知是“人杰地灵”或者“穷山恶水出刁民”;现在的理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实说,按这些常规的解释思路,有时感觉因果关系很明显,有时又未必然。特别是像谭其骧先生考问过曹树基兄的问题:宋代江西、福建文化极盛,但到了明清江南兴起后,江西、福建都衰落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大约1994年前后,我注意到学额作为社会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兹事与各地科名盛衰深有关系。但手头有任务,一直腾不出手来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分析论证。2003年志平来读研,我便建议他以此为题撰写他的硕士学位论文。
为了控制工作量,志平的硕论聚焦于清代的长三角地区。内容以考订学额的分布及变化为主,也延伸到学额与中举、中进士人数的相关分析,以及各学定额与取额的制约因素。之后我们又一起做了些工作,于2013年合作出版专著《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应该说,自从志平着手做他硕士论文的相关工作,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挖到了一个品位很高的学术富矿。
一方面,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学额作为传统时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关系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中间既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也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竞和自我保护。志平在本书上篇的结语中称之为“一种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乡绅编制”,其说法有当与否容可商榷,但于其重要性仿佛得之。
与此同时,以往的相关研究非常薄弱。前贤虽有不少人在研究中涉及过此一问题,但都是局部、侧面的撕扯。或从制度上加以考订,或对汇总数量进行估算,或就局部地区具体事件所涉及问题加以探讨。尚未出现基于每一学额单位各时段逐一落实,形成时空序列数据,然后逐级汇总、深入分析的正面研究。
按理讲,这种状况,继续用它作博士论文选题是完全可以的。但稍后志平回来跟我读博,我们讨论他博论选题时,都感到任务过于艰巨。全国范围,拿不下;做局部地区,相当于做个半拉子,不甘心。于是我们干脆另起炉灶,让他做了个《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于2010年通过答辩。
他博士毕业后,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把这项清代学额研究善始善终,做出个可供学界参考的成果来。好在他这些年比较顺利,2017年就解决了正高职称。先一年他以《清代学额研究》为题拿到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就建议他干脆利用这一机会,将清代学额做一番系统完整的清理。他心无旁骛地做了五年,于2021年通过结题。我又鼓励他继续修改补充,争取申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终于完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巨著。
作为志平曾经的导师,看到他做出这么大的成就,欣喜之情自不足与外人道。在此略言几句与学术相关的感受。
首先,我想郑重感谢志平,把传统时代文教定额制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将清代所有设置学额的单位逐一清理,加以考订,形成了纵(时间)成线、横(空间)成片的时空序列数据,堪称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为之后关于清代定额制度的研究厘清了很多误解,奠定了一个新的基准面。
当初我建议他做这个题目,其实是想解答我本人内心的一个疑问:定额制度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那些举人、进士较为密集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的学额多?
应该说,这个疑问在志平的硕论中已经做过一番解答。当时分清前期(1690-1723)、中期(1726-1760)、后期(1870-1904)三个时段,对各县的学额与中举、中进士人数加以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学额与其中举、中进士人数呈显著相关,而中举人数与中进士人数呈高度相关。这一结果虽不能有效解释一些州县学额相等或相差不大,而中举、中进士人数却相差悬殊的现象,但不妨碍总体上得出定额制度对于地方文化发展有较大积极影响的结论。
现在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全国范围,上述认识要做比较大的修正。根本无需借助于数学运算,仅凭简单逻辑推理就足以判断:学额分布与举人、进士的数量分布不可能存在太强的相关关系。举人、进士的分布往往呈现出较强烈的空间集聚;相比之下,学额的分布要均衡得多。就是说,相对于举人、进士的数量分布,学额的分布有其独立的空间逻辑。
在本书上篇第十章,志平对学额与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展开了讨论。该章第一节,志平开宗明义指出,学额制度设置的目的是养士而非选拔人才。他认为:“清代学额制度是政治文化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考虑到童生应考需要付出高昂的求学和应试成本,而这一成本“是诸多平民家庭无法逾越的障碍”,志平指出,“童生成为生员之后,绝大部分并不会进一步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因此他认为,相对于选拔人才,清代学额设置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
为增强说服力,志平还特地用将今证古之法,以其个人求学经历中的观察和感悟,来阐明基层普通百姓的生活逻辑。他将其概括成一句话:“谁都想未来有更好的生活,但把眼前的生活过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作为同样生长于乡村、通过求学而改变生活路径的本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承认,触摸到了隐藏在其中的生命温度。
显然是格于研究旨趣,这里面有个问题志平没有进一步追问:清代为什么要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基层绅士?或许他觉得答案不言自明。在此我想强调一句:这是清代维系其大一统的文化纽带。
这根纽带具体如何发挥作用,是另一个问题。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根纽带的设计实在不可谓不精妙。
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袤的伟大国家,其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一大特征就是地域不平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平原水乡到青藏高原,各个向度的水热条件差异都极大,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天然带有多元的特征,在文化上要形成并维持一体的局面,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自不能不煞费苦心。
学额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资源,对它进行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要公平。然而公平的实质,却颇难衡量。从考试来说,自然应该凭文取中,择优录取。可是考虑到不同地区文教水平存在落差,就全国范围而言总体落差还相当之大,若一味凭文取中,又必然导致不同地区间的不公平。于是,清朝采取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策略,将取录额数直接分配到各基层单位。这样,虽导致不同省份的童试取录标准相去悬殊,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总算大体保证在同一成长环境中的录取公平。而且,当相邻地区童试竞争度相差过大时,学政官员还可以通过学额调拨等措施予以临时补救或永久调整。
秀才是宰相之根苗,童试是科考的起点。学额设置和运作的制度精神与之后乡、会、殿各试的制度精神一以贯之,共同构筑了清代数百年的文化大厦。
在此我也须指出,本书虽然为清代文化定额制度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基准,但它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很多相关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或重新研究。在此分三种情形稍加举例。
其一,学额制度本身范畴内的,例如,清代制定府州县学定额的依据,早在志平做硕论时便高度关注。亲自参加过科考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称:“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页)但是这种种等差,如何折算成具体的学额数量,迄未找到明确的史料依据。包括清代在具体的学额划拨、裁撤事例中,决策者如何制定额数标准,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二,学额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例如,科考当中的代际差异。上文多次提及定额制度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域之间的机会均等,事实上,除了地域差异,代际之间也存在着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至迟到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金钱作为高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已经使高科举功名黯然失色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24页)。此言就颇有代际差异意识。本人感觉,代际差异、代际公平是中国历史上颇为重要的一大问题,历史上很多朝代面临一些周期性的困境,其实都是没处理好代际之间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就清代而言,代际问题应该比之前历代都要严重得多。这里面,一是清代延续时间长;二是清代人口增长快,而且增幅大。从顺治十二年(1655)到道光三十年(1850),总人口从1.19亿增加到4.3亿。(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与此同时,学额制度却稳定得多。因此,就入学难度而言,不仅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南北方不可同日而语,同一地方的清初与清中期、清后期也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这种代际差异,应该纳入相关研究视野。
由于史料记载的局限,上述两个问题要充分展开都有相当大难度。也许永远都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学术研究如行远路,首先需要明确目标,哪怕只是个大致方向。
其三,与学额制度相关的,可谓科举社会史问题,例如科举考试中的各种成本,各地与科举相关的习俗,等等,若能加以进一步研究,无疑将大大深化对传统社会的认识。这方面涉及面众多,凡有涉猎者自不难想见,在此不缕述。
最后,我也应该指出此书的一些不足之处。按世俗观点,此书的文字过于朴拙了一些。全是干货,很少有读来令人口齿余香的段落。不过说老实话,我个人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缺点。这样的著作,是供人留在案头备查,不是捧着朝夕诵读的。因此,个人认为越干瘦越好,节约了读者的成本。
希望志平再接再厉,继续面壁,早点做出姊妹篇来,将清代的文化定额制度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
(本文系新书序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