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读《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修史“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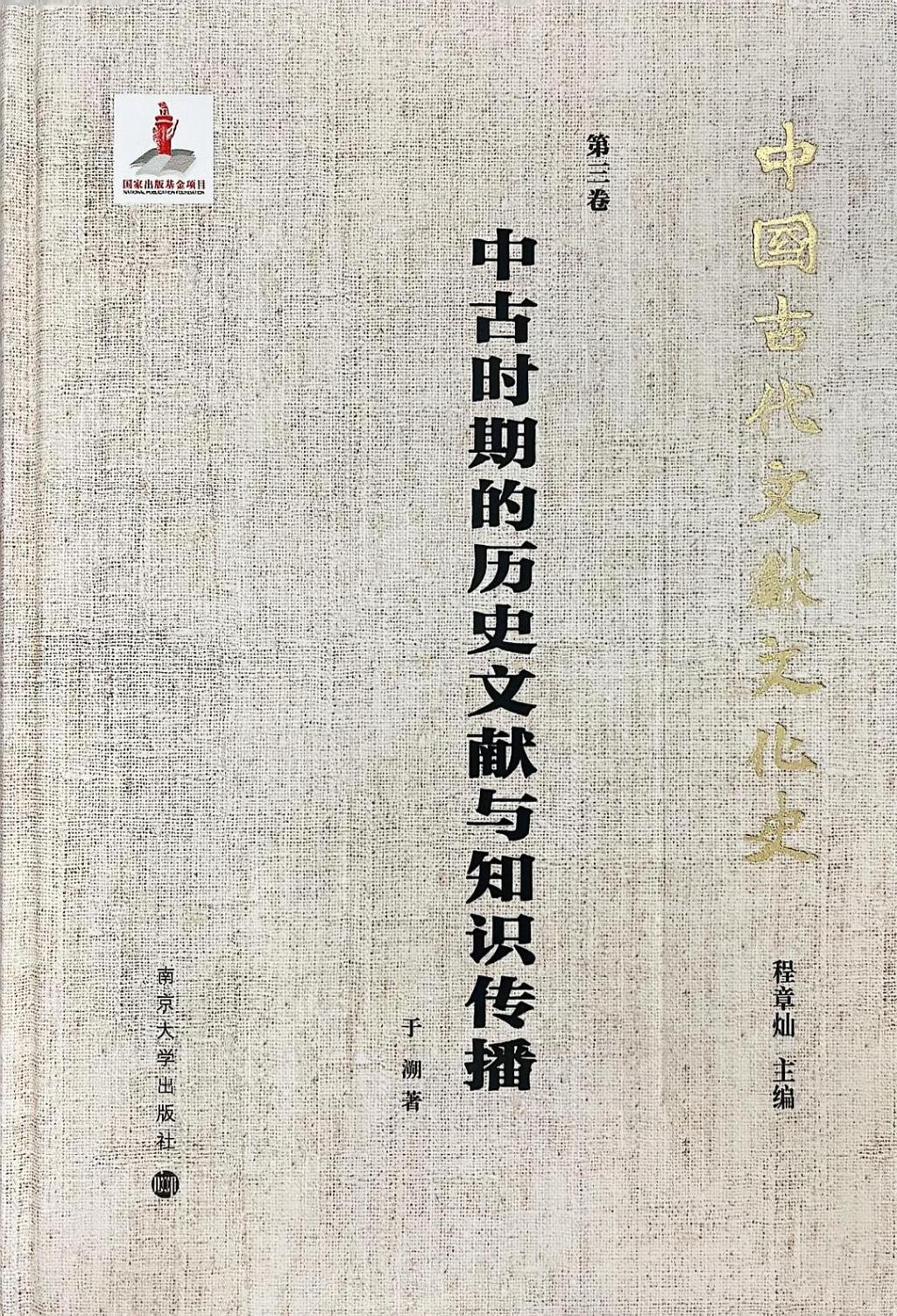
《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于溯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247页,70.00元
历史并不存在,除非它被记录;由此,何人记录、如何记录、记录什么、为何记录这些而不是其他、最终又如何为人所获读,几乎可说是历史学的元问题。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世界异常活跃,从《史记》到《史通》,实现了史学和史部文献的最终诞生。此后,史部一直稳居四部,列经部之后,直至清末民初四部之学为分科之学所取代为止。
历史文献为何在汉唐之间爆发,史部究竟如何得以确立,其间过程线索丰富、细节密布。学者已从历史背景、时代风气、修撰制度等方面,做过大量有益探讨,似已题无剩意;然而,当这一传统议题来到兼备技术敏感和文学文本分析功底的于溯笔下,竟得以生面别开。《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一书,多视角呈现了汉唐时期历史文献的“文化史”,作者在绪言强调,这有别于“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文献学以及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的史学史”(1页)。嵌在书名中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两个关键词,分别对应了本书探讨中古时期文献的两条线索,其一是历史文献的制作,另一则是历史文献的传播,两条线索在书中并行又交互,共同演绎出中古时代历史文献发展史的一曲交响。大体而言,本书的内容和方法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中古著述的技术维度
围绕汉唐时期史籍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特点,本书前三章提出三个工具概念,分别是卷子本、模块化和记忆体,为今人理解汉唐时期的文献生产、传播与使用提供了结构性背景。
纸虽然发明于西汉,但直到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后才得以大幅普及,至魏晋时代逐渐取代简牍,成为文字记录的主要载体,进而带来书籍形态的变革,直接结果就是卷子装的出现,这也导致“卷”取代“篇”成为中古典籍的基本单位。《盈握:卷子装与中古书籍史》一文,在统计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十三种正史和《隋书·经籍志》、两《唐书·艺文志》等相关历史文献的数据后,提出中古书籍史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十三种正史中,再没有出现篇幅超过两万字的单卷,且单卷字数借由内容析合而趋同(18页);其二,在汉唐时期目录中,二十卷以下的小书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百卷以上则低于百分之三,且大书种类单一、主题集中:经部礼类,史部正史、起居注、仪注和谱系类,子部医方和类书类以及集部总集类(22-23页)。于溯认为,对于这两个现象,卷子装的物理形态都提供了理解路径。前者源于只手持握对卷轴体量的约束,后者则在于多卷并联、团队作业的模块化搭建为大卷帙书籍制作开启了有效路径,进而使得官方组织快速产出“皇皇巨著”成为可能。这类图书目前可知,以曹丕在位期间(220-226)官方修撰六百八十卷的《皇览》为最早。由此,于溯重新探讨了太康年间(280-289)《中经新簿》四部分类出现的原因,她指出甲乙丁三部大体还保留着和《七略》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丙部是不见于旧有目录体系的新部类,而丙部所辖史记、旧事、《皇览》、杂事几类文献,虽隐约可见后来史部的特点,但在当时则全无清晰意识。丙部所收书目更为共同的特点在于卷帙浩大,因此,“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大书彻底破坏了《七略》体系,从而将目录学推入四部时代”(30页)。可以说,在中古图书大规模生产和知识分类变革的背后,卷子本都是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除了单卷这种可视化模块单元外,《隐蔽的网络:中古文献中的模块化书写》一文继续探讨了弥漫于中古时期文献内容中的模块化现象。模块化既不同于文学写作中的典故使用,也有别于类传叙事中的格套化呈现,而是一种功能项的情节单元,有长有短,有显有隐,人物和道具皆可调整,因此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中古文学写作中的“拟”和文论中提及的“袭”“傍”“借”“偷”等手法相关又有别。比如文中例十所谈及的一类情节:主人公在有条件占用丰厚战利品的前提下仅选择书籍或其他别有深意之物甚至分文不取以显示人物节操(46-47页)。于溯强调,这类叙事模块一旦形成,不只影响文献生产,也会因其在文献中的反复再生产,进而经由阅读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这点不难理解,毕竟,生活也常常戏仿文本。因此,模块化作为中古历史文献潜在的书写技术和实践惯性,应成为今人阅读文献、理解史事时需格外注意的现象。本书所收《互文的历史:读〈五柳先生传〉》一文(191-202页)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个案分析。
模块化的影响不限于生产环节,也造就模块化的阅读方式。中古时代,大卷帙文献往往以单卷的形式传播。这种独立的文献形态,加强了文献的可记诵性。《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一文提出“记忆本”的概念,强调模块化阅读带来记诵之便,使得肉身也在纸张、碑刻之外成为文献的一种重要载体。中古时期“记诵故事”井喷的背后,存在着无数后世已然消失但当时则不容忽视的文献“记忆本”,它们在“在获取、携带、传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写本所不具备的优势”(64页)。中古时代写本大量“同音异文”现象的背后,正是“记忆本”参与文献制作和传播的痕迹。可以说,和类书出现的背景一样,“记忆本”既出于对占有海量知识焦虑的克服,又进一步催生了知识的积累与迭代。
找回历史文献的“初语境”
文献最初为何/何以诞生?是本书多篇文章共同探讨的主题。王朝史是政治运作的产物,也是文献运作的产物。《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从“文献环境”的视角讨论了西晋建国史的书写及其特点。众所周知,撰成于唐初的《晋书》以“好用小说家事”而受人诟病,于溯指出,这“与其说是唐修《晋书》的特色,不如说是东晋以来诸家晋书传递给唐修《晋书》的特色”(85页)。永嘉之乱造成的文献散佚,皇室衰微导致的组织不力,都构成东晋编修晋史的“真实困境”,因此,在“档案类文献”缺席的背景下,大量“依据于回忆、传闻、访谈等形成的记述”的秘闻与佚事便流入正史,这与其说是史家的主动选择,毋宁说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权宜行事。因此,通过《晋书》的书写,我们不只能够看到文献环境对文本样态的具体塑造,也能看到社会记忆在正史文本形成过程中的切实参与。
《蜡以覆车:范晔〈后汉志〉考》一文,以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中出自《宋书·谢俨传》(已佚)的一则关于范晔《后汉志》废弃后被“蜡以覆车”的记载为线索,探讨范晔《后汉志》的修撰与篇目,在前人基础上得出若干有益的结论,比如,以绢帛为载体表明《后汉志》已定稿,范晔《后汉志》本有《食货志》和《刑法志》,另外还有《艺文志》,这些论断不只对前人关于南北朝史学史的相关认识有所推进,也提示了文本载体媒材蕴含的历史信息,以及传志互文中埋伏的正史篇目结构调整的线索。《隋炀帝的遗产:〈隋书·经籍志〉的形成与早期史志的统计问题》一文,与前人多从目录学角度探讨《隋书·经籍志》不同,转而将之视为“一篇史志”,揭示出这份文献与炀帝东都书库、五代史志修撰的方式与贞观时代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此来探讨《隋书·经籍志》中的数据参差、书名变化和图书毁佚等问题。
如果说上述三篇文章以具体案例揭示了中古历史文献的制作背景,书中还以其他实例提出阅读中古历史文献可择取的微观语境。比如由《水经注》中关于《桥玄庙碑》的记载复原东汉乡里的石刻景观(《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以特定文化符号和文体选择,探讨曹操父子的文学实践与曹魏建国史塑造之间的关系(《宣传:建国史与中古文学的开端》),通过复原沈迥的人生经历提取《归魂赋》中的地理信息(《归魂:纪行赋的道里信息》)。文章主题各异,但都力图将被后世归于不同门类和学科的文献,置于其诞生的“原境”中,进而释放其中蕴藏的历史信息。
超越汉唐的史家匠心
《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与广义合本子注说》一文在全书别具特色,是对汉唐时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代表的中古史注的探讨。裴松之《三国志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名篇,不仅为中古史研究者所熟知,也是治魏晋南北朝史学史领域的熟题,特别是近代以来因受到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格外推崇,而受到治佛教文献学、近代学术史等专业学者热议。在此背景下接着讲,于溯将问题进行了拆分:其一,《三国志注》为何采取如此这般的形式?这一形式为何遭致刘知幾(661-721)的频频恶语(即“按之使入地”)?其二,陈寅恪所说“合本子注”到底是什么?他为何给予裴注如此高的评价(即“举之使上天”)?
元嘉五年(428),宋文帝(424-453年在位)下诏裴松之(372-451)为《三国志》作注,令其“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以弥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缺憾,由此,裴松之将“多辞”并抄于“一事”之下,以“务在周详、以备异闻”为第一原则实为奉旨答题。从《三国志·上注表》来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一项要求明确的国家项目,因此,“掇众史之异辞,补前史之所阙”的结果,既源于项目委托人的要求,又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否则援引汉晋之间逾百部书而成的《三国志注》,绝无可能短期完成。如此前胡宝国先生指出的,东晋太元(376-396)以降经济好转,带来图书大规模聚集,至宋文帝元嘉八年,秘阁所藏《四部目录》已达到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参《从会稽到建康》,《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212页)。文献规模短时间巨量增长,客观造成同一史事出现众多“异闻”,由此,孙盛《异同杂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都是这一知识背景下的产物。在于溯看来,这类“史注”文献在排列异辞的同时,还将“最终决定权交与读者”,使得“读者有更强的参与感”,而就功能而言,这类史注则可视为以“事”为单位的类书,得以“一书在手、众本在握”(150页);但刘知幾并不关心这类文献的知识背景,也未对裴注进行逐条仔细分析,在他看来,这些书无疑是将修史过程中的“吐果之核,弃药之滓”又捡了回来(151页),是职业史家所难以接受的做法。
陈寅恪在1933年《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古时期佛经文献之“合本”(即同文异译的汇编),“子注”虽亦谈及,但尚未直接冠以“合本子注”。此后陈寅恪又陆续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3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陈述〈辽史补注〉序》(1942)、《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1948)、《杨树达〈论语疏证〉序》(1948)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谈及“合本子注”的概念,并最终称裴注《三国志注》是深受“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的产物,又“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于溯在梳理学术史之余,辨析了陈寅恪所论合本与同时稍早佛教史学者吕澂(1896-1989)所论之异同,指出陈先生关注的重点,不仅在于这种“事类相从”的文献形态,更是一种“基于此文献形态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认为这种文献方法,与为当时学界所推崇的“比较研究法暗合”,皆意在“求同异之所寄”(131页)。
经过上述对裴注为代表的史注和陈寅恪“合本子注”的辨析,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援引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中的一句话,来定位《三国志注》为代表的史注与陈寅恪所谓内典“合本子注”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纵无师承之关系,必有环境之影响”。从汉唐时期的知识史脉络出发,再结合本书所提供的书籍生产和传播技术背景,裴注《三国志》这类文献的出现或许别有渊源(比如古文经学的方法、类书的相互影响等),但这些史注确实与佛经译本共同面对着同事异辞(译)迭出、亟待对比辨析的“时代现实”,而以“事”为单位加以排比条列,也确实是卷子本时代最有效的呈现方式。胡宝国先生曾对南朝贵能博闻、知识至上的学风有过精彩论述,他同时指出,在这一风气中,“事”成为活跃的知识单位,同样弥漫在史学领域(《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188-189页);进而,“事”相应也成为重要的知识模块,在文献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历史文献修撰处于现实世界和修辞世界的交界面上,记什么和怎么记取决于史家的知识传统、个人才能、技术条件和修撰目标,而历史文献的阅读则是一个经由作者写作、文本媒介(卷子、碑刻或记诵)再到读者理解的辗转流动过程,其间每个因素和每个环节都可能带来信息的损益与变形。这些围绕在文献周边的因素和环节,都会影响文献对“历史”的记录。由此,当我们借由文献通向“历史”之前,势必需先对“文献”本身的历史做一番检视。于溯在绪言中借用卡尔·休斯克的话说,书中的十一篇文章并非要去建构一个历史时段的全貌,而是希望从尽可能多且各异的切入点去观测“中古历史类文献”这一核心命题,进而“各个部分能够彼此照亮对方,共同来阐明更大的整体问题”(4页)。以读者立场来说,本书通过对中古历史文献兼具理论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细致阅读,尤其从技术维度加以讨论,无论是整体背景的解释,还是具体个案的分析,都拓展了观察汉唐历史与历史文献的视野,具有方法意义,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
诚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文学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这句话无疑也适用于历史,历史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史学和史料亦然。就此,《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一书的意义不止于“对着讲”,而在于难能可贵的“接着讲”,不作简单归因,而是尽可能呈现关联性,打开另一重视角,提供另一种可能,释放中古历史文献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以具体案例证明,在经验、感受力和手艺的交互幻化下,熟题亦能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