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铜于山:文化心灵诗学的形上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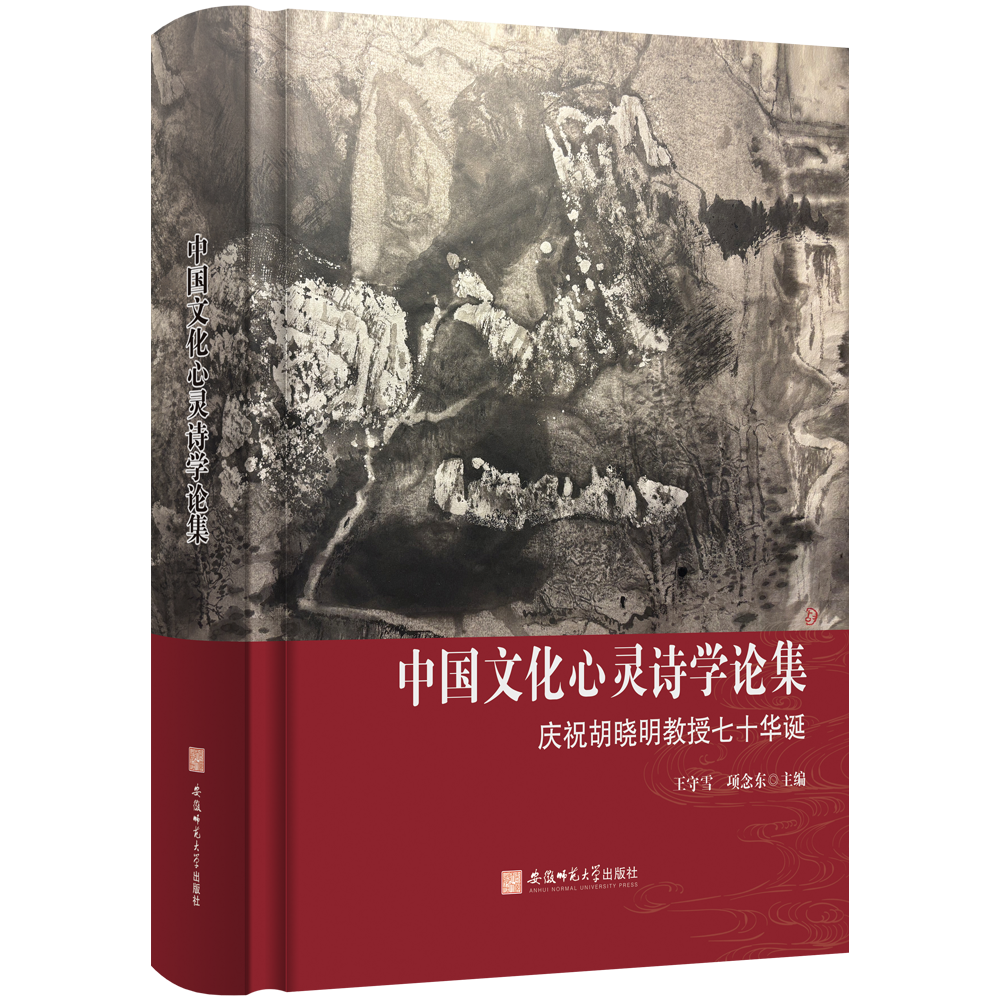
《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王守雪、项念东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文化心灵诗学作为具有创造性的当代诗学理论,不仅有了初步的理论构设,而且在这种理论的运用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文化心灵诗学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诗学研究在纵深层面的发展,有着多重的原因。其中文化心灵诗学所蕴含的形上意识代表了这一理论建构具有很高的反思起点,有着对人类文化命运发展的深切忧思。文化心灵诗学将诗学研究引向当代人文学的发展道路,也说明这一理论具有与时代同步、与人心同步、与文化同步的特点。
从形上的角度看,人是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相统一的。物质性存在作为基础一旦形成之后,就需要精神性存在的加持、引领和促进。离开了精神性存在,纯然物质性存在的人,也就难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精神性存在的养成和丰富的过程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其中诗学心灵的维护至为关键。
在所有艺术表达方式中,诗歌最能够表达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底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创作诗歌成为精神性活动的最为极致的能力,也最能够体现人之精神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诗歌形成的传统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故乡,或者说体现了这个民族创造的最美的精神性存在。胡晓明先生指出,“中国诗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最高表现,是中国人文精神至美之花。”(《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中国诗,无论有多少复杂的变化,无论有多少历史的形态,其背后总有一种强大而又无形的力量,我称之为‘中国文化心灵’。”(同上)文化心灵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文化心灵诗学,其所指向的精神性的内涵也非常广泛。胡晓明先生认为,年轻人的价值观、心灵品质、思维能力、感悟能力等,都离不开诗教的传统熏习。(《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这些通过诗教熏习而来的能力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心灵所应该具备的内容。

《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新书发布座谈会现场,胡晓明(左)与戴兆国(右)
人们常常将诗和远方相提并论。去远方可以让人转换当下生存的环境。一个新的所在往往会唤起人们内心新的希望。同时,对一般人来说,远方也意味着理想和追求。远方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一种空间和时间意识。胡晓明先生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提出了诗歌空间体验具有张势和敛势,张势中既有儒学,又有庄学精神,敛势中,亦与大易之幽人、孟子之独善等思想有关。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感受,则有两个系统,一是屈子型的,以主观时间为优势,一是庄子型的,以客观时间为优势。这种对中国传统诗中的空间和时间体验的概括本质上带有形上的思考,具备哲学美学的丰富韵味。
如果不去远方,到不了新的所在,我们还可以有诗。人们眷念诗,就要读诗、写诗、评诗。通过这些活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诗的层面得以展现。生活中有了诗,意味着心灵能够得到放飞,人因而能够得到闲适,享受安居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人类的精神故乡。文化心灵诗学指示了人类过精神生活的方式,那就是读诗、写诗、评诗。人与诗歌为伴,就能让心灵保持活力,富有感性能力。感性能力是人从事一切艺术创作的最为原始的动力。从意志哲学的角度说,人激发生命意志的根本动力源自于心灵,源自人的精神性的追求。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人类的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心灵深处的活力。这是文化心灵诗学反思过程中的形上指向。“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考订者与叙述者,而喜作发挥。”(《诗与文化心灵》)喜作发挥,也是一种文化心灵的自我激发,是人之作为主体的生命意志的高扬。这是人之为人所有的文化心灵的本质体现,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高级动物的心理活动,不可能造成某种文化的结果。
文化心灵诗学采取整体诗学的视野来拓展对诗的观照和理解,也是对其理论形上意识的凸显。具体而言,胡晓明先生认为文化心灵诗学的理论拓展包括三个方面,即诗观立基、兼顾三才、采铜于山。
诗观立基是指用中国诗学的诗观作为心灵诗学的基石。这种立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文艺学与诗学合一,一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文艺学。核心内容包括三项,以心为本体,以兴为动力,以文为经脉。胡晓明提出文化心灵诗学本质上是心学化的诗学,以此区别于历史化的、体系化的、关系化的、西学化的、生命意识的诗学研究。此五种诗学研究取向缺少对诗学研究本体的观照,总体上属于形而下的诗学研究。从具有反思意识的角度看,这五种当中的生命意识的诗学研究,应该说带有某种形上的追求。以兴为动力强调诗学要发挥诗教对人性的激醒的作用。这其实是对人性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兴的动力和心的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此处的心是心物合一、古今相连、生生不息、心心相印的心。心不是分析的心,而是整体的活生生、富于历史深度的心。这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及的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等概念。胡晓明特别提到心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源自士人通过诗的创作、吟诵、传播,向大自然采气。诗人因为其诗心的激发,能够保持诗人出于精神的上升状态,而不至于堕落。其实,诗人不仅向大自然采气,也时刻向人世间采气,向历史过往的人生、向当下的人生、向未来世界的人生采气。这是诗的生命力的根本来源。以文为经脉,是指以一切具有交错纹理的文化的创造物为经脉。古典诗学之所以能够与书画乐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就在于其内涵的交错的文化精神。
兼顾三才是指诗人要有才学识,采铜于山则是对诗学研究材料的要求。两者是文化心灵诗学研究方法论的两翼,即谁在研究,从哪里开始研究。文化心灵诗学的方法论是对古典诗学研究的回顾与现代重建。这种重建是“为了人的成长、为了生命的美好发育而建立的一大系统:人与自我关系的诗性、人与社会关系的诗性、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性。”(《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
如何做到兼顾三才和采铜于山,胡晓明指出最为基本的进路有很多,但是最为重要的有三项,即学艺双修、诗思互进、诗化生活。
朱光潜先生提出,不通一艺莫谈美,不通一技莫谈艺。从美学反思的实际来看,由技而艺、由艺而美的进路有时候也能通过形上的沉思予以打通。此所谓通也可以理解为朝向通的境地,而无绝对的彻头彻尾的通。文化心灵诗学提出学艺双修其实隐含了这样的思路。
诗思互进对于主动进行反思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日常的生活之表现。本质上看,“哲学乃思之诗,文学乃诗之思。哲学是从精神的深处往内看世界,文学是从精神的深处往外看世界。哲思乃人因不满于对现象世界的平铺直叙而生的根本之思。其所求者不在于对一事一物得一解释说明,而在于探求事物之所以如此,何以如此的本根或本体。故而,哲学之思考总有形而上的向度,总有对精神无限深处的探掘,以期得到终极性的答案。此答案即便永远不可得,然亦是哲学无穷追索的方向。文学者乃借用文字之组合排列,以特殊的兴发手段,阐释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文学绘描的世界,充满着艺术的想象。文学之想象是从精神深处逐次地向外描摹,于情感的激越中表达对物理、人事的了解,最终以求得心灵的释放。哲学之思是思中有诗,文学之诗是诗中有思。”(《道谭》)诗思互进就是本于思中有诗,诗中有思。这是一切文化心灵活动的常态。
正是诗与思的互进主宰了人的精神生活。这在诗人那里体现得更为突出。胡晓明说,“文人的创作,呈现着他们精致、典雅,富有着人文光辉的心灵生活。”(《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其实,真正的诗歌创作和评论都要有采铜于山的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说,采铜于山是对文化心灵寄托的本体反思。这其中也蕴含着理一分殊的形上意识。这一点早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就有过表达。胡晓明先生在结语万川之月中提及古今中西之学人皆有向善的心灵取向。诗学研究要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达到烹天得渣,炼道取髓的结果。中国传统诗学的发展脉络,由道德理性为起源,中经道德超人文之感性心灵,最终以人文境界为依归,一心开三门,殊相归一境。其中形上的反思意识殊为突出。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心灵感受的诗人对中国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意义非凡。
本文为《中国文化心灵诗学论集》新书发布座谈会的发言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