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装豆奶:豆浆的“现代乳品化”转型
欧洲营养科学的产生和传播不仅提高了牛奶在亚洲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豆奶的地位,促使豆奶生产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工业化。早在汉朝早期,中国就发明了豆浆。豆奶最初并非作为食物,生豆浆中含有蛋白酶抑制剂、低聚糖(易引起胀气)和脂肪氧化酶,容易引起消化不良(Huang 2008,52),因此,传统观点认为豆浆是中国的一种古老食物,事实却与之相反,豆浆是在18世纪或19世纪才成为中国饮食的一部分,当时人们发现,豆浆经过长时间加热后,很容易被消化。
虽然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由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在街头售卖的豆浆和油条是香港工薪阶层最常见的早餐或零食,但许多人认为这些只是“穷人的食物”,营养价值低。在20世纪40年代香港遭到日本侵占的动荡年间,数万香港人惨遭不幸。当人们把大米、花生油、少量肉类和燃油存储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食品店时,有人建议把大豆也作为战时重要的粮食储存,但在当时遭到了拒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的医务总监(1937年至1943年)司徒永觉爵士(Sir Percy Selwyn Selwyn-Clarke)在自传中回忆:“当我建议用后者(大豆)作为蛋白质来源时,就遭到了立法会中一些中国同事的反对,他们抗议说大豆是用来喂猪的。最后还是中国实业家罗桂祥先生对大豆产品的重视,才使得香港及其他地区的人认识到大豆的宝贵价值。”(Selwyn-Clarke 1975,62)
如果说19世纪末欧洲人在香港推广牛奶,是出于道德因素的一种战时防御措施,那么20世纪30年代豆奶的工业化则是出于增强中国人体质的目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增强国人体质变得尤为重要。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称,香港豆奶的工业化旨在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营养丰富、价格低廉的食物。对他来说,豆奶业的发展体现的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期间,许多中国难民生活在肮脏不堪的难民营中,普遍营养不良,豆奶的出现给难民们带来了福音(Hsieh 1982)。罗桂祥开展志愿服务,为难民提供牙刷和牙膏等日用品,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许多难民都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这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1,严重的脚气病不仅会影响神经,还会导致身体疼痛和虚弱,甚至心力衰竭(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9)。1937年,朱利安·阿诺尔德(Julian Arnold)在上海出差时做了一次题为《大豆——中国的“奶牛”》(“Soybeans—The Cows of China”)的演讲,罗桂祥这才开始了解大豆的营养价值。得知豆奶中富含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与肉类和牛奶接近)、矿物质和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适中,罗桂祥萌生了生产豆奶的想法,豆奶成本低、营养丰富,能够改善难民的体质。为了帮助难民生产豆浆,罗桂祥及朋友给难民们送去了几百千克大豆、1口大锅、1台石磨,一些用蚊帐制成的过滤网,并教他们制作豆浆的方法。罗桂祥先生说,没过多久,许多脚气病患者就可以下地走路了。看到如此积极的效果,1940年,罗桂祥在铜锣湾创办了第一家豆奶厂,就建在外国乳业巨头“牛奶公司”的前面,那时“牛奶公司”主营新鲜牛奶,主要服务当时香港的欧洲人和富人。
罗桂祥承担起了向公众宣传新兴营养科学的道德角色,并以此作为其豆奶产品营销的策略,努力将豆奶产品从“传统中国食品”转变为“现代乳品”,并将产品命名为维他奶(“含维生素的豆奶”),装入玻璃奶瓶中,以便消费者看清里面的豆奶。“维他(vita)”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生命”,是“维生素(vitamin,也译作‘维他命’)”一词的缩写,这也为现代豆奶戴上了科学的光环。把这种饮料命名为“豆奶”,而不是中国常用的“豆浆”一词,并将其装入玻璃奶瓶中,都旨在将罗桂祥的现代豆奶从豆制品(被视为传统、中式且低级的食品)类别中抹去,重新将其解构为优质、现代的“西式”奶。为了进一步加强维他奶与牛奶之间的联系,罗桂祥甚至也采用了送货上门方式,与“牛奶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罗桂祥还仿照“牛奶公司”经营西餐厅的战略,在香港九龙半岛的旺角开了一家“维他茶餐厅”,出售维他奶和中国甜点(Cai 1990,30—31)。
鉴于豆制品悠久的食用传统,再加上道德因素以及精心策划的营销策略,罗桂祥预计豆奶会很受欢迎,然而茶餐厅开业第一天却只卖出了9瓶豆奶,这让罗桂祥倍感惊讶。在20世纪40年代末,维他奶的销售遭遇失败,可以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会每天都食用豆奶,是因为豆奶属于“寒性”食物。根据中国的体液理论,食物本身自有“寒性”或“热性”特质,大豆食品和豆奶属于“寒性”食物[Li(1578)2003,595]。社会学家尤金·安德森(Eugene Anderson)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仍然会根据盖仑的“热—寒”、“干—湿”分类理论选择食物、设计食谱(2005,142)。豆浆属于“寒性”食物,而油条属于“热性”食物,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人的早餐会把油条和豆浆视为完美搭配。体液理论在香港影响深远,这可以从一件轶事中反映出来: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指责罗桂祥“不道德”,销售不健康食品,因为她认为豆奶“太寒”,“不健康”(Cai1990,20)。即使到了21世纪初,西敏司和陈志明就香港食用豆制品的情况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不宜多食豆腐或豆奶,因为豆制品属于“寒性”食物(Mintz and Tan 2001,125)。在这项研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她的母亲在煮豆浆时,通常会在里面加入一块生姜(“热性”食物),以降低豆浆的“寒性”。
20世纪30年代,罗桂祥试图将维他奶定位为牛奶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相信营销信息中所宣传的维他奶的营养价值,或者从更广泛的方面说,是不相信豆奶与香港新建立的牛奶文化存在相关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维他奶迎来了一个转折点。由于生产技术和营销策略的转变,维他奶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最终战胜了“牛奶公司”的新鲜牛奶。维他奶采用了瑞典开发的超高温灭菌(UHT)加工技术,并使用利乐砖无菌包装,这样产品更轻便、更结实,可在超市出售,使之一跃成为人们参加户外活动的最佳饮料。由于便于携带,维他奶不再强调与牛奶的相似性,而是重新定位为一种用于解渴的国际化“软饮料”,成为社会各阶层获得现代新身份的希望。从1975年开始,维他奶推出了一系列新广告,有一句粤语广告词“点只汽水咁简单”尤为成功。为了树立维他奶“现代”“西式”的品牌形象,公司聘请了许多名人,如艺术家萧芳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演唱英文歌曲,被打造成一名国际化的现代女性;以及温拿乐队,堪称港版“披头士”。有了这些名人在广告中背书,维他奶吸引了大量痴迷外国电影和摇滚文化的年轻消费者(McIntyre,Cheng,and Zhang,2002)。通过这些营销策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征健康和科学的维他奶转型成为一种现代的户外和休闲“软饮料”,成为20世纪70年代“乐趣”“幸福”和“放松”的代名词。如我们所见,维他奶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在营销中对文化符号、软饮料文化的全球化以及现代包装技术的巧妙操纵。
20世纪70年代,维他奶作为一种“软饮料”在年轻中产阶级消费者心中的重新定位取得成功,这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背景分不开。维他奶广告中所展现的现代生活方式,充满了自由、乐趣、快乐和休闲意识,受到了新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认可,这得益于社会重大改革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和安全,特别是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发生后实施的“十年建屋计划”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大的作用(Tang 1998,65—67)。这种新中产阶级和香港本地身份认同在香港当时多样化的休闲活动中,以及国际化的流行饮食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由于香港住房密集,游泳和野餐等户外活动就成了新型核心家庭每个周末的仪式性活动。20世纪70年代的人,也是第一代经历了香港经济繁荣的人,获得了一个现代、国际化的身份。归属感开始在流行文化中盛行,粤语流行音乐(外国人称为Cantopop)成为主流(McIntyre,Cheng,and Zhang 2002)。随着与“其他人”(来自内地的新移民)的互动不断深入,香港身份也不断升级。在1976年至1980年期间,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数超过10万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维他奶成了香港新身份和社会阶层独特的象征。维他奶不再是外国牛奶的替代品,或者只是用于满足弱势群体营养需求的一种营养丰富、能量高的食物。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维他奶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中新有闲阶层食用的现代“软饮料”,这些有闲阶级喜欢玩乐、性格外向、对其他文化充满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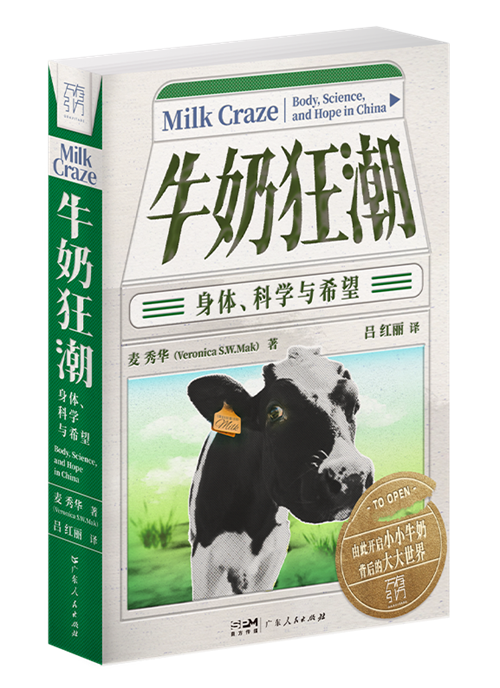
本文摘自《牛奶狂潮:身体、科学与希望》,麦秀华(Veronica S.W. Mak)著,吕红丽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