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签契约:人文知识分子能否和社会大众重归于好?
2025年4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公开拒绝特朗普以冻结联邦资金为威胁的整改命令,被视为美国高校对抗联邦打压的第一声枪响。就在前一天,哈佛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美国及其大学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指出美国社会对精英大学的不满由来已久,而自二战以来美国高校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亲密合作也早已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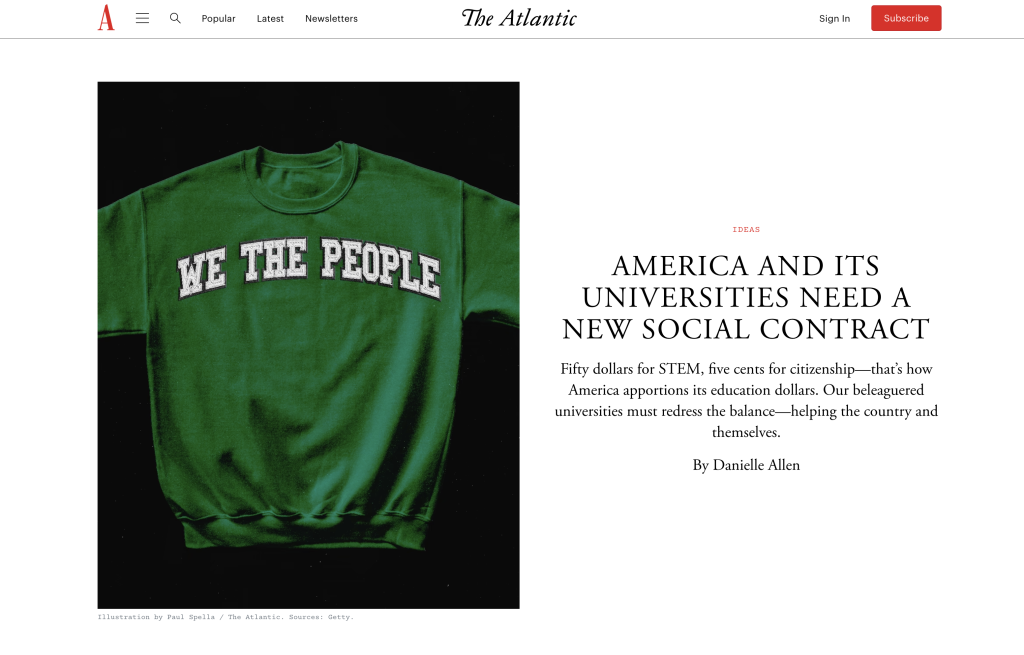
艾伦的这篇文章写得可谓是九转十八弯。文章一开始,艾伦温情脉脉地叙述了自己如何一路走来,在象牙塔里享受“思想生活”(life of mind)的乐趣的同时,仍旧不忘对社会的责任。在短暂地哀叹了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思想生活的冲击之后,艾伦突然指出美国学人之所以能够过上这种超然世外的生活,实际上是仰赖于联邦和大学在80多年前所达成的一份“社会契约”。在礼貌性地对这份老契约的逝去表示哀悼之后,艾伦又突然笔锋一转,祭出大棒,批评这份契约从签订之日起就蕴含了毁灭的种子。
艾伦所说的“契约”,其实指的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二战结束前后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总结了战时“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运作经验,主张永久性地将“政府资助科学、大学服务国家”这一机制制度化。艾伦认为,这份报告奠定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信仰:联邦政府应当拨款让科学家们专心进行基础研究和成果发表,而政府部门和工业界则承担将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的责任。换句话说,二战期间科学研究所展现出的巨大军事与经济效益,使政府与产业界心甘情愿地为科学家背书,将他们从必须向公众解释研究社会意义的责任中解放出来。这一分工机制此后不断制度化,并逐渐演化为一套默契的信条:无论多抽象或前沿的基础研究,其价值终将以“提升国家安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形式兑现。
然而,战后持续八十年的和平时期让这份契约暴露出新的裂痕:社会大众已不再直观感受到科学研究的公共价值,而科学家们也早已习惯以“学术自由”为名,回避对社会责任的回应。一方面,美国大学日益精英化,使普通民众难以相信大学的存在可以促进自己的福祉;另一方面,大学又高度依赖政府拨款,使得“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制于政治博弈。所以,当愤怒的民众与对学界左翼极端反感的联邦总统结成同盟时,美国大学便注定难逃此劫。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5日,人们聚集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大学约翰·哈佛雕像前。
所以,这份曾经被奉为美国学术神话的契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在这里,身兼古典学家和政治理论学家的艾伦显出了真身:
“过去80年,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可以用三个词概括:STEM,STEM,还是STEM!到2022年,由于长期的政策导向,美国每年在人均STEM教育上的联邦投入大约为50美元,而在公民教育上的投入仅为每人每年5美分。那求仁得仁(you get what you pay for),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既不了解、也不尊重自治与自由所需制度的社会。”
所谓的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就是所谓“理工科”。到这里,我们才看出来,艾伦所不满的并非时下特朗普对哈佛的打压,而是80年来美国大学和理工科的蜜月以及对文科的冷落!
艾伦认为,这份契约只是狭窄地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意义的目标,完全忽略了美国的立根之本:公民力量(civic strength)。如果美国大学从来没有把培养出具有宪政精神、多元开放态度的公民作为自己的责任,只是一味遵守“科学家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信仰,那么遭到一个不具备公民精神的社会的反噬,只能说是自食苦果。
文章的最后,艾伦给出了一些关于大学和社会公众签订新契约的建议,比如:
在理工科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加入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导向
增加大学招生,缩短本科学制,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
大学录取时将K–12阶段(即从幼儿园到高中)是否获得“公民教育印章”纳入录取标准,将美国的宪制民主的历史以及多元主义的训练开成大学必修课
创立新的商业模式来削减对联邦资金的依赖
艾伦这一番抽丝剥茧后最终把特朗普打压大学的时事和文科在大学的式微联系在一起的笔力,让我感到钦佩。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科生,她的这些论点,以及那些对文科功用的鼓与呼,让我感到困惑。一方面,艾伦所指出的社会与大学(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失去信任,绝对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艾伦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似乎在中国已经部分地实现了。那么艾伦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呢?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是否也需要和社会重新签订一份契约,来挽回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按照艾伦的说法,范内瓦·布什的老契约最终造成了象牙塔内居民社会责任感的解除,但是为什么这个现象专属于理工科?难道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所处学科的关系,就会永恒地自带社会属性,和象牙塔外的社会保持沟通?
很显然,这不是事实。在今天这个重视AI、大数据、医学的时代,社会和理工科所签署的互信条约依然有效。在中国,政府与理工科达成了“科技兴邦”的契约,社会与理工科达成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契约,以及工业界和理工科达成的“研发费用不能省”的契约,仍旧十分稳固。相反,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的契约变得十分模糊——社会大众越来越难以理解日益专门的人文学术对社会有什么责任?当代大量的中国人文工作者既没有封建帝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签订的“学而优则仕”的契约,也没有启蒙知识分子与社会签订的“引领思想”的契约。
大量无约傍身的人文学术青年,只能蜂拥后退,在象牙塔内互相拥挤踩踏,在面临生活的物质窘迫和社会意义感缺失的双重功能打击下,冲着塔外高喊:文人不谈契约!在今天,人文工作者似乎都更依赖旧的社会契约所确立的那个以“无用之用”为标榜的大学体制来为自己代劳,向社会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
其次,即便我们认可艾伦的批评,人文学科的价值并不应该用“增强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那么她所提到的第三标准“公民教育”,是否能够重建文科和大众的关系?
这点在中国的情况更加有趣。首先,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讨论美国“公民教育”的确切内容是否要移植到中国。我们要讨论的是,就算一个国家的人文学术承担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教育,那么它是否就能赢得社会的信任?艾伦建议,各种研究申请应当有社会责任的导向。这在中国不是问题。各种项目基金和研究课题的申请要求中,社会责任都是首要关切。艾伦建议,国家历史和公民教育要纳入必修课。近代史、公民教育在中国早就是必修课。但很显然,这些都没有改善日益恶化的文科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症结在于,艾伦似乎简单地把人文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等同于“公民教育”,但是大部分人文工作者并不认为人文学术的主要意义是公民教育,而社会大众也不会因为人文学科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就以身入局。
从张雪峰用最直白的方式道出社会大众对选文科专业的态度,到《南风窗》刊出的那篇出圈文章《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文学术和社会大众的老契约(政治资格、经典传承、文人风骨等价值标准)已经岌岌可危,象牙塔只会给人文学术留下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有越来越多抱有旧时人文理想的青年,将会不得不走出象牙塔,面临为自己谋生和正名的任务。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能在象牙塔之外,不放弃人文理想,重新续约社会,这是一个真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我所谓的这个人文学科和大众的契约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这份契约必须要以那些从事“狭义的人文工作”的劳动者为签约主体。这就是说,一些传统的证明方式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人们可以论证:人文博雅教育可以培养一些基础能力,这些能力可以用于进行其他更社会化的工作。学文科可以考公、从事法律或者咨询等工作,在业界生存。但是,这些论证都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在这些论证里,人文学科只是一种手段,需要类似公务员、律师或者咨询行业这样被大众接受的有价值的行业来背书。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仍旧会好奇,为什么不直接去读法学院,而要走人文学科这样一条弯路?
因此,若要实现社会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真正互信,我们必须要求契约的签订方继续从事较为狭义的人文实践:以人文知识为生产资料,以文字、思想、评论等为产出成果,并以反思能力、知识整理能力及文化审美能力为其核心竞争力。
其次,这份契约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自得其乐”“经典传承”“无用之用”“永恒智慧”这样的论点,并不再天然地适用于所有人文知识分子。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应重新开放其价值体系,使诸如社会介入、现实回应、知识转化等取向,成为学科传统内部同样受尊敬的方向。这是人文学科提供给社会的offer。反过来,社会则应当提供一个体面的薪水和工作声望,以确认人文学术的社会贡献得到认可。唯有在双方的共同调整与互相成全之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契约才有可能达成:社会大众得以分享人文学科的成果,并由此激发参与这一事业的动机与热情;而人文学者也能在自身的工作中获得价值感、社会认同以及相对体面的收入与生活保障。
仿照艾伦的做法,我们或许也可以据此列出这份“新契约”的两条核心条款:
甲方:人文工作者
乙方:社会大众
一、甲方应当将乙方所关心的有关个人精神生活的问题,纳入自身的考量,并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产出。甲方内部应当形成对这种工作方式的正当性认同,甲方部分人员应当甚至应当将这种工作方式作为其首要工作方式。
条款解释: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启蒙知识分子,以及本世纪头十几年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和人文知识界的连接者。然而,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与社会签订的契约仍旧是某种政治契约。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紧密绑定,使得人文学界和大众的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固。在政治性(资政辅政)和非政治性(纯粹学术)之间,或许仍存在一种社会公共性的可能。人文工作者应该将当代人的具体的精神困境(诸如孤独、抑郁、内卷、过劳、原生家庭、低能量、社交媒体成瘾、大龄焦虑、亲密关系危机等)纳入自己的考量,避免过快地将这些问题变成理论兴趣,而是要用文学、历史和哲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人文描述和指引。
二、甲方和乙方应当共同合作,培育出一个象牙塔之外的拥有公共声望、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人文工业界”。
条款解释:当代人文工作者谈到去“业界”(industry)的时候,往往说的是所谓“转码”(学编程进入大厂当码农)、“转法”(重新读法学院)和“转咨”(咨询行业),然而这些“转”从某中程度上都是对狭义的人文劳动生产方式的脱离。虽然人们通常不把教育界称之为“业界”,但是事实上,非研究机构的教育界(比如高中和文理学院)往往也是人文工作者的备选项。不过在中国,除了少数超级中学可以提供“狭义人文工作”的机会之外,大部分中学教育活动都意味着新的工作方式。至于中国的所谓“文理学院”几乎全部依附于综合大学,故而并非象牙塔之外的“业界”。不过,有趣的是,当代中国一些玩出花样的“留学辅导”机构承担了“教育业界”的功能:为了提升藤校录取率,精英家庭逐渐摒弃竞赛、体育等传统赛道,转而通过早期人文教育(尤其是古典学)构建子女的文化资本,以此制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总体来说,人文工作者的各种“转”都是因为缺乏一个成熟的、具备社会声望和盈利能力的人文工业界。我们看到了一些人文工业界的苗头:转型后的传统文化媒体(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人物》《新周刊》以及澎湃思想新闻中心等)、知识付费平台(得到app、三联中读、看理想、豆瓣付费课等)以及自媒体平台(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小宇宙等)都在尝试构建一个“狭义人文工作”可在象牙塔之外持续发展的平台。
读者至此或许已经看到,我与艾伦的契约论有根本的不同:艾伦以“公民教育”为核心重建的所谓社会契约,本质上仍旧是象牙塔内部的人文工作者和社会的政治契约,在这份契约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对大众民主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我非常怀疑这种政治契约是否真的能够重燃社会大众对人文学科的信心,从而让时下日益艰难的人文工作者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我所谓的这份“新契约”,本质上是一份象牙塔外部的人文工作者和社会签订的商业契约,在这份契约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对当下公众精神生活议题的阐释与引导能力。
毋庸讳言,这份新契约将人文学术的工作方式定位为紧密围绕大众需求的商业生产与流通,至少从思路上,已经不同于人文工作者对人文理想的初心追求。而且,这份新契约中真正的乙方,或许目前也并非“社会大众”,而是广义的城市新中产。对这些担忧,我们可以或许考虑这么几点:
第一,新契约并非对象牙塔的取代。相反,它允许象牙塔内外的人文工作者都成为甲方; 如果象牙塔许诺扩大容积率,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文工作者都愿意进入,但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它正在缩小容积率。一个日益拥挤的象牙塔只会让社会大众望而却步,而塔内居民也只能被迫继续创造远离大众的“象牙塔特供产品”;
第二,即便我们假定这份新契约目前所能寻找到的,具有消费需求和能力的乙方只是城市新中产,也没有问题。甲方需要一个过程去建立商业模式、培养消费习惯并扩大消费市场。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商业比喻的本体,那么似乎这个人文商业化的思路也没有那么可怖——“扩大消费市场和群体”恰恰意味着,大众对于人文学术的兴趣、理解、尊重甚至依赖正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