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国家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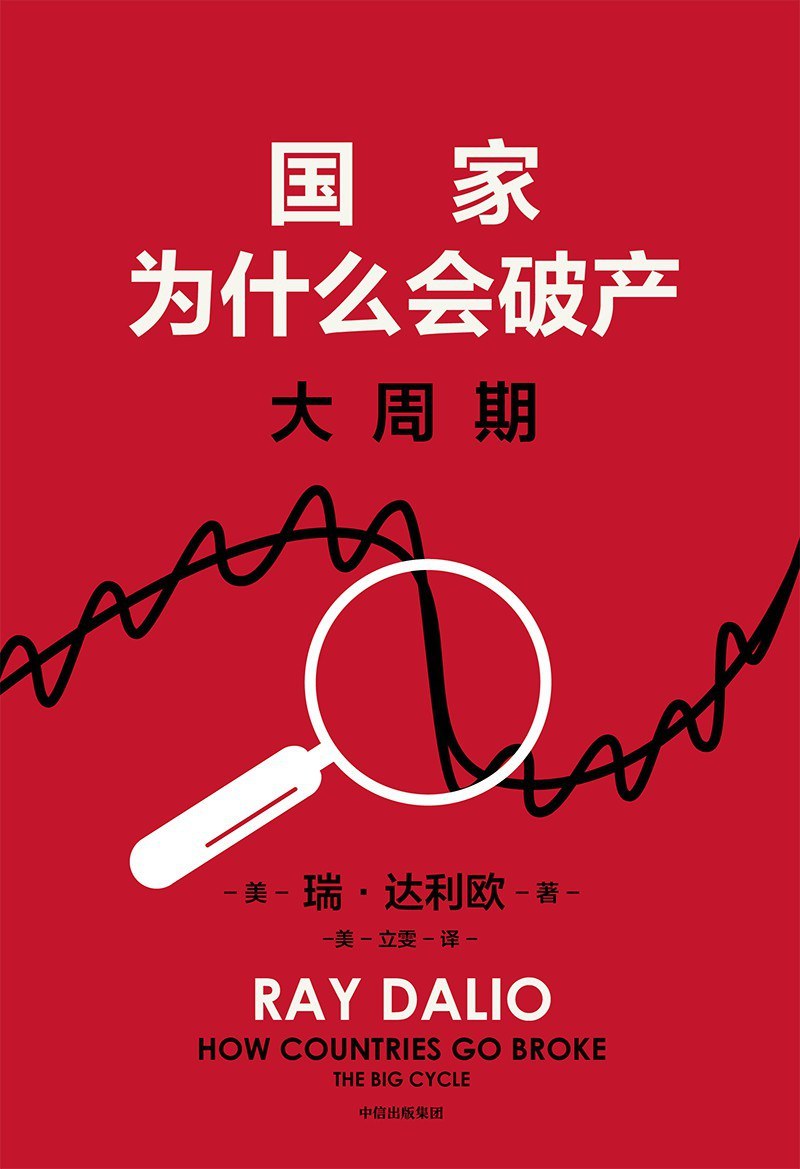
《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美] 瑞·达利欧著, [美] 立雯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6月版,138.00元
美国著名投资人瑞·达利欧(Ray Dalio)的新著《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How Countries Go Broke:The Big Cycle,2025;立雯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6月)从完稿(书中多次提到正在写作的2025年3月,英文版也是3月出版)到中译本出版,仅三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翻译出版速度是不多见的。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提到他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称)开始了合作关系,是四十多年来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在该书中译本封底勒口的作者介绍是:“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他出生于纽约长岛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26岁时在自己的两居室公寓内创办了桥水。经过50年的发展,桥水成为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位列‘美国最重要的私营公司’榜单第5位(《财富》杂志)。他曾入选《时代》周刊‘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并跻身《福布斯》杂志世界前100名富豪行列。由于他独到的投资准则改变了基金业,投资界著名刊物CIO称其为‘投资界的史蒂夫·乔布斯’。”该书中译本随书赠送一本“解读本”手册,印有十五位国内外金融机构人士、经济学家和财政官员的推荐语,另外还有五篇评论文章。该书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经济决策人士、银行家、金融机构人员、金融投资行业人士、经济评论员等。
债务增长有限制吗?政府巨额债务是怎样形成的?那些重要的储备货币大国真的会破产吗?如何向决策者建言除弊兴利?——总之,中央银行和国家因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破产?这是该书论述的核心问题,也是作者和他的主要读者群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的非专业和非主要读者来说,可能会更关心的问题是假如国家破产了,会怎样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普通打工人,没有什么可以破产的,但是国家破产之后如何活下去也是有时候要想的问题。
全书开头就是作者撰写的“中文版序”“我为何分享此书”和“如何阅读本书”,非常简洁地讲了该书的写作目的、信心和给读者的建言。作者自信满满,快人快语,对于像我这样完全不懂金融投资的读者来说是很好的导读。比如作者说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建议你通读全文,会帮助你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如果不是,建议你只需阅读字体加粗部分即可(“如何阅读本书”)。另外,“如果你只打算阅读这本书的一章,那就读第8章,它涵盖了这些内容”(“我为何分享此书”)。我想这不仅是让非专业读者节省时间,更是因为在其他章节中密密麻麻出现的那些数据图表是不容易搞懂的。
作者说:“这本书阐释了我们当前共同面临的债务、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背后的运行机制。”这是对该书主旨最简洁的表述。“在过去50多年的全球宏观投资生涯里,我逐步洞悉世界运行规律,得以成功预判重大趋势。这要求我必须深刻理解驱动经济与市场变革的因果关系。在这半个世纪里,我将对现实运行规律的认识及应对之道总结成各种原则,并将其输入计算机决策系统,这正是我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今我已75岁,把我毕生所学传递给他人成为我人生现阶段最重要的使命,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启发。”(中文版序)
接下来在“我为何分享此书”的论述中,作者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分享我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50多年来所领悟到的那些珍贵、永恒且普适的见解和原则。我相信没有人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拥有更好的资源来获取这些见解和原则。……我深信,当这些理念传递到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手中时,世界会运转得更好。”“你将全面且深入地理解‘整体大周期’,这个大周期是由大债务周期和其他重要周期驱动的,包括改变国内政治秩序的大政治周期,以及改变世界秩序的大地缘政治周期。写这本书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帮助你理解这个‘整体大周期’是如何带来这些大转变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正临近这样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我为何分享此书”)应该注意到,作者强调他与读者分享的是“我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50多年来所领悟到的那些珍贵、永恒且普适的见解和原则”,在“如何阅读本书”中说:“我还希望传递一些妥善应对现实的永恒普适原则,这些原则已加注了红点,并以斜体显示。”
在这里我想起近日在“经济学人书评”(The Economist Book Review)看到的一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新书介绍,亚历克斯·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的《迟钝工具:为什么经济理论无效……却仍不可或缺》(Blunt Instrument: Why Economic Theory Can’t Get Any Better…Why We Need It Anyway,MIT Press,2025),该书针对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诘难:金融市场的危机一次次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并不能预测现实,那么经济理论要来何用?罗森伯格用“钝器”来形容经济理论,坦率指出经济理论在预测上的失败早已是结构性的、无法修复的。他梳理了从边际主义、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与行为经济学的主流演变,指出其共同盲点:经济学建构的“模型世界”并不映射“现实世界”,而是构建在理性人、完全信息、均衡状态等理想假设上的封闭系统。这种系统根本无力面对现实的非理性、动态性与复杂性。这些对于经济学主流的批评是经济学界早就讨论的问题,该书的新贡献是认为经济理论即便“无用”,仍必须理解它、捍卫它。罗森伯格指出,经济理论虽不是预测工具,却在规范制度、塑造博弈结构方面具有关键意义。特别是博弈论的诞生提供了文明社会对抗掠夺性、非合作性行为的策略工具。我的理解是,经济理论不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术士,但仍然是建构经济制度、维持经济运作的设计师和看护人;不能单纯依赖它作为决策的依据,但是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不能抛弃它。这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作用的审慎态度。
由此再想到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30-2014),他提出的有关新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使许多被忽视、回避或者是被以僵化方式看待的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也使许多正在萌动中的发展趋势被敏锐地揭示出来。那是真正帮助许多普通人改变了处境。贝克尔从1985年5月开始在《商业周刊》上每月发表一篇专栏文章,至2004年共坚持了十九年之久。贝克尔的经济理论思考总是与当下的社会热点紧密相关,极大地提高了以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诺奖得主贝克尔论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樊林洲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收入了他发表在《商业周刊》上的七十八篇专栏文章,他说“我们相信这些专栏对问题分析的准确度很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不过,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性的思考的确能让人更深入地理解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同上书,361页)至于“我们对公共政策的建议究竟有没有影响力”,他认为“我们相信这些文章是有其影响力的,不过,效果的显现往往是缓慢而迂回的”;“事实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对立的利益团体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平衡点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357页)。因此,“我们对于政策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样也是采取从长期的观点来做判断的”(359页)。说明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判断这些公共政策讨论的真正影响力,至于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自有其利益博弈、权力运作的民主程序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经济学家对于理论能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很好说明。
从历史的视角来认识现实和预判未来的发展,这是《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的“大周期”理论的重要方法论。思考“五大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目前的作用,“这将有助你明白‘历史重演’是怎样发生的,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145页)。“由于历史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因果关系,并为当前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视角。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历史案例来思考在现有的情况下,哪些事情是逻辑上可能发生的。”(148页)历史借鉴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正如作者所言,“为了帮助我们想象未来,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历史的教训”(155页)。但是简单地把“历史重演”视作规律性的周期,仍然值得商榷。
《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大债务周期”理论解释货币体系的崩溃乃至央行及国家的破产过程,第8章“整体大周期”是作者认为全书中最重要的章节。“这是因为本章探讨了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最强大且最重要的力量,并展示了这些力量如何以及为何反复推动历史进入大周期。……同时,通过揭示过去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我们理解那些曾经难以想象的发展现在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未来仍有可能发生。”(143页)
在“机器如何运作”这一小节的开头,作者肯定了世界万物的有规律性,所有变化如永动机般周而复始,因此必须洞悉其内在机制。他的方法是为因果关系建模,用自己的模型来押注市场走向。作者所创建的计算机专家系统的原则是“决策系统应基于永恒和普适的原则,这意味着其应当能够解释所有时间范围内以及所有国家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发展”(144页)。然后,从宏观层面上总结了最重要的五个驱动因素:一,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二,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三,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四,自然力量(干旱、洪水和疫情);五、人类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创造。“这些力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最重要的历史进程,推动市场和经济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趋势线周期性波动。”(145页)
这五个驱动因素也就是作者所讲的“整体大周期如何运作:五大力量”,“我们如今已处于二战结束后的‘整体大周期’中的第80个年头,这一周期大体上正以经典的方式展开,并将催生剧烈的变革,只有通过在历史背景下想象这五大力量同时互动,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变革”(146页)。
关于“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短期周期始终存在,其平均持续时间通常约为六年,上下浮动三年,并且将累积成“大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平均持续时间约为八十年,上下浮动二十五年。“永恒的和普适的(历经数千年且在各个国家皆如此)驱动大债务周期变化并引发重大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因素是,相对于现有的货币、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数量而言,不可持续地创造出了大量的债务资产和债务负债。这总会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银行挤兑现象。”(147页)这就讲得比较清楚。
应该注意的是“永恒的”和“普适的”这一提法,在前面“我为何分享此书”的论述中也强调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分享我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50多年来所领悟到的那些珍贵、永恒且普适的见解和原则”,要分享的是“妥善应对现实的永恒普适原则”。然后,这里的“数千年”和“各个国家”的说法就是对“永恒的”和“普适的”而言的。在该书前面第一部分也有相同的表述:“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跨越不同国家疆界……”(11页)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出现了私人借贷的记录,借贷的可以是银或消费品,也有免息的或约定利率的记录(参见马克·范·德·米罗普[Marc Van de Mieroop]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1997、1999;李红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95-196页)。然而这些借贷行为在当时是如何产生“大债务周期”的,需要通过具体史实来论证。另外,还需要通过史实来说明数千年前的借贷不但形成了“大债务周期”,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是如此。遗憾的是达利欧在书中没有提供这样的史实论证,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作者早已阐明他的出发点并非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开展这项研究,而是以全球宏观投资者的身份进行研究(引言,2页)。在我看来,如此肯定地断言“大债务周期”在数千年时空中的永恒性和普适性,给人的感觉是为了强调作者对过去一百年所有重大债务周期的“仔细研究”和对过去五百年中更多案例的“粗略研究”(2页)在更大得多的时空尺度中同样可以得到带有永恒性和普适性的验证。但是古代史学者米罗普告诉我们,即便是到了古亚述时期,我们或许还会高估了此时信贷运作的重要性,有很多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210页)。
现在回到作者论述的“大周期”晚期阶段。这就是引发大周期终结的萧条和战争阶段之前的阶段,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晚期阶段。“那么,当前的形势究竟如何?此时此刻,美国以及所有其他主要国家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同时这些国家的内部秩序正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和分裂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自然灾害频发且代价高昂,而令人惊叹的新技术也在不断涌现。”(148页)这是很有概括性的表述,接下来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情况: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购买本国债务;选择性冻结债务和/或没收“敌对国家”的资产;通过延长债务期限和/或债务货币化实现债务重组或违约,以削减债务负担(类似于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所采取的方式);实施没收性税收和资本/外汇管制,以防止资产外流;重新评估/管理政府资产;创造新型货币。在这里作者相当明确和审慎地补充说,并不是断言这类事件必然会发生,同时也在犹豫是否应该提出这些可能性,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过度恐慌(148页)。
然后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论述的是国家内部存在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这些波动会累积成内部秩序的重大转变。“这些权力斗争在所有的政府体系、各类组织甚至家庭中基本上都以相同的方式展开,因为应对这些斗争的方式深植于人性之中。”(149页)在民主国家中,选举周期与经济周期大致同步,新领导人上台之初通常会有一段蜜月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为当选而做出的重大承诺通常变得难以兑现,支持率逐渐下降,往往会导致为了保住权力而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讲到这里马上切入当前现实:“在我撰写本书的2025年3月,这些动态正在美国发挥作用。事态的发展通常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而经济状况又主要取决于影响市场和经济的短期及长期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所处的位置,尽管外生性事件(如干旱、洪水、疫情以及重大的国际或国内冲突)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150页)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内部的所有治理秩序都会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作者特意以斜体强调:“当民主制度失败时,专制制度便会取而代之。”(同上)作者进而联系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民主如何转变为专制的有价值的描述,柏拉图把推动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变革的人称为“煽动者”,操纵公众舆论、煽动情绪,并使用非常手段来获取权力。他们通常会激起民粹主义情绪,承诺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往往以牺牲真相或理性讨论为代价),并通过宣传和恐吓来获取和扩大权力。这些领导人通常会对货币、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进行激进改革,并往往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专制化。这一过程最终常常导致民主被更为集中的独裁政体取代(151-152页)。这的确是在观察美国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种种变化时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讨论的问题是作为大周期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出现单边主义(各国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和多边主义(各国追求全球和谐共处)两种模式的波动。目前的情况是多边主义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单边主义正在崛起。“尽管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转变起初令人震惊,但很快就被正常化。例如,就在我撰写本书的几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的言论还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样的时期,令联盟关系往往会随着局势的快速变化而迅速改变,胜利比忠诚更为重要。”(154页)这些论述都很精准。
第四个因素是“自然力量(干旱、洪水和疫情)”,干旱、洪水和疫情正在增加,且代价日益高昂。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范围内更紧密的接触等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最后就是新技术的发明创造,科技的巨大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影响所有领域的思维。科技进步与其他四种力量密切相关。当科技进步得到良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支持时,其发展速度会比在不良环境下更快。但如果科技进步依赖于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就往往会导致金融泡沫和泡沫破裂(156页)。
以上是作者关于“大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现在可以回到第二部分的开头引言,正是“大周期”五大力量驱动的重大变化导致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破产的事件反复发生。所谓的“破产”是指央行失去正常偿债能力,尽管可以通过印钞避免债务违约,但大规模印钞会导致货币贬值并引发通胀性衰退萧条(88页)。这是对“国家为什么会破产”最简洁的解释,也是被公认的经济理论。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一方面各国政府与央行的关系并不一样,并非所有央行都会接受政府指令;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对国家金融信誉的打击。因此关于“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还存在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原因。
关于如何应对大周期带来的挑战,作者认为从原则上来看“最强大且重要的力量是人们如何相处。人们如果能够共同应对问题和把握机遇,而不是彼此争斗,就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不幸的是,尽管科技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性并没有太大改变,因此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157页)。对于人性的认识是一个有着多种维度的和相当复杂的问题,作者对于国际关系语境中的人性的看法表明,丛林时代的人性仍然占主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状况的。
作者在书中一再谈到对特朗普任期下美国变化的忧虑,很有现实的针对性。他指出“特朗普总统在国内、国际、经济、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上带来了显著转变,使其更具侵略性、自上而下/独裁性,右倾、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这些政策转变以对抗性增强和合作性减弱为特征(同时也体现在多边组织的瓦解和单边主义的加剧上),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类似转变相呼应,最近一次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时期”(220页)。“在我写这段话的2025年3月,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刚刚上台执政,美国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重大债务问题;(2)国内冲突导致采取更严格的半专制政策来压制反对派及其左翼政策;(3)与中国及其盟国的国际冲突加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从全球领导者转变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参与者;(4)气候变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5)美国处于一场科技战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输不起。”(245页)这些描述和分析都很准确。
从美国扩而言之,世界各国都面临相类似的严重问题。“按照我的衡量标准,当前形势类似于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情况,以及历史上许多国家在许多时期的情况,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周期的第五阶段。在第五阶段,各国普遍负债过重、治理效率低下、内部分裂、受到其他国家威胁,因此很容易出现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要为提升国力而战,更愿意通过参与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来获得胜利。”(321页)
作为投资人,达利欧提出的建议是要意识到这些极端行动带来的风险,并随时关注局势变化。最好的方案是采用他提出的“3%三部分”解决方案(削减支出、增加税收、降低利率,使赤字减至GDP的3%),同时配合一个“和谐的去杠杆化”过程。“展望未来,主要目标将是同时提高生产力和减轻债务负担(这也将降低债务和货币的价值)。”(324页)对于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作者一方面对技术性的进步感到非常兴奋和乐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非常强大的技术进步很可能不足以压倒来自债务、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等力量的逆风(342页)。作者相信并且一再提醒读者的是,“未来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现在到那时将感觉像是穿越时空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许多现在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公司和个人将会衰落,而那些现在处于低谷的将会崛起。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非常不同,其程度是我们无法预见的”(342页)。
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呢?达利欧说“最佳方法是依据概率行事,进行良好的多样化投资,并坚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则。至于身处哪些地方最为有利,我认为是那些正确把握这些基本面的国家”(同上)。但他没有说具体是指哪个国家,只是描述了那些国家的一些特征。无论如何,作者在全书末尾想到的最后一个原则是“如果你毫无担忧之心,那就应该感到担忧;而如果你忧心忡忡,那么反倒无须过于焦虑。这是因为,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担忧会让你有所防备,而对这些问题毫不在意则会让你暴露在风险之中”(343页)。这是对的。
读这本《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很自然会想到之前读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2;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该书讲的“失败”主要是指国家的衰退、贫困,与债务问题引发的国家“破产”还不太一样,但是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作者研究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历史变迁,研究结论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对国家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虽然制度学派自十九世纪以来就是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但是该书所谈的“制度”有新的、深刻的内涵——分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两种制度又各自划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实行了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前者就是专制独裁,公众没有选举权、罢免权,统治者垄断权力且不受制约,制度和政策成为权贵攫取和维护利益的工具;后者因前者而建立,市场竞争、自由贸易等受到极大压制,统治集团尽可能地压榨社会财富。该研究还指出,尽管也有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会坚持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同时搭配上一定程度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错配是脆弱的,持续不了很久。“分配和运用权力的能力最终会成为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从汲取性转向包容性。”(《国家为什么会失败》,67页)作者这里举的是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型之前的例子。
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共同的视角,那就是对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在研究主旨、视角和理论体系方面有较大差异。那么,债务周期的历史模板与政经制度的历史模板哪个更为真实地决定历史的变迁?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与投资人的知识背景、学术语境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结论,这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