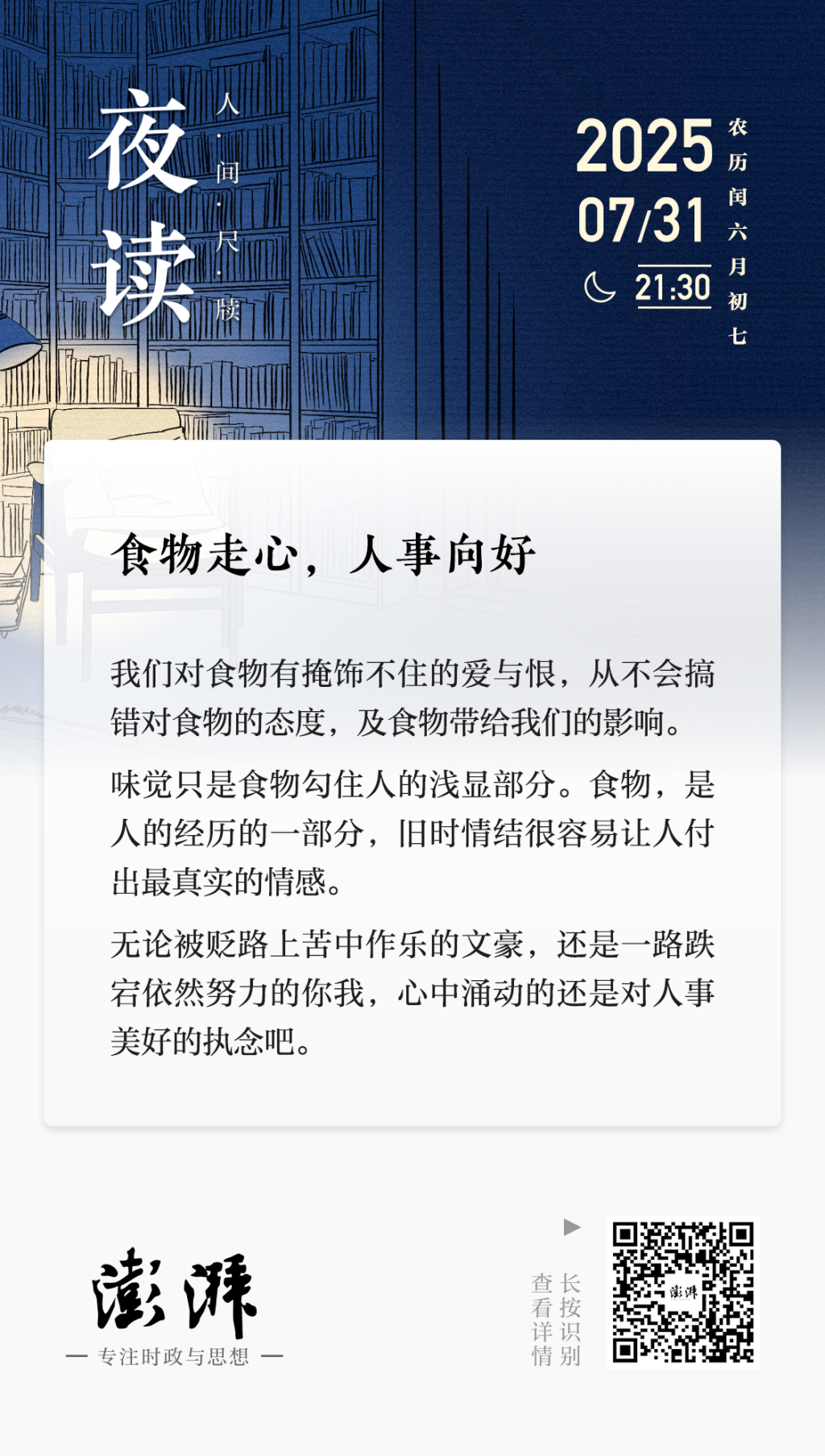夜读|食物走心,人事向好
活过半辈子,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馋食物的时候,馋虫并不是幕后主使。
平日里,当一个人脱口而出“今天就吃这个了”,起作用的是一种愉快的经验。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共识。譬如,我对紫苏、薄荷、荆芥,都是起初嫌弃后来嗜好。往简单了说,这是我适应了那些奇怪但是丰美的草叶的味道;往不简单了说,这是被神秘气息勾了魂。
食物的好味道深远无边,但不会独占一个人的味觉,让你只听它号令,也不会限制别的食物争宠。爱了东坡肉,也会迷上回锅肉和火腿肉;吃尽各种茎叶,依然会在下一个机缘中被新的茎叶所折服。新的体验往往受益于旧日的经历,我第一次喝罗勒汤就感觉舒适,这要感谢薄荷、荆芥们先前推送过的幽微感觉。
我们对食物有掩饰不住、按捺不住的爱与恨,从不会搞错对食物的态度,以及食物带给我们的影响。正如同样一款香菜,有人甘之如饴——几十年里,我只要点饺子,十有八九点香菜馅的;有人却恨之入骨,以至于“讨厌香菜日”都出来了。
我们的评判,例如“好吃”,其实只是潦草的体验。我们很少深想美味背后的奥秘,那种让人的肠胃和意识瞬间受惊、迷失的感觉,究竟出自哪里?
其实,味觉只是食物勾住人的浅显部分。食物,是人的经历的一部分,而旧时情结很容易让人付出最真实的情感。
前不久的梅雨季节,我和妻子、妻妹、堂侄女徜徉在皖西北一个小县城里的美食夜市,点了很多好吃的,有现卤的猪尾巴,有现烤的“马知了”,有羊肚包,有炒凉粉。妻子和妻妹时隔多年返乡,只恨肚子太小,只恨时日太短,遗憾未能一次性尝尽故乡美食。
夜市里蒸腾着食物的烟气和香气,让我若有所思。食物的地方习性,才是一条美食街的灵魂。这里的干扣面,别处没有。南京的盐水鸭、洛阳的水席、高邮的汪豆腐,也是天下独一份。离开洛阳多年,我在南京最想念的,还是年轻时喝过多回的铁谢羊肉汤。
热播剧《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回到长安,第一件事就是抱着日思夜想的胡麻饼狼吞虎咽。这架势,是暂时逃出生天的侥幸,是活下去的欲望,是为保护女儿蓄的力,更是曾经缠绕五脏六腑的暖意。
我奶奶生前对我极好,她只请求我办过一件事,就是为她代买冰糖。那是我在县二中住校的时候,抽空买了冰糖,骑车送回村里。把黄色的老冰糖放进嘴里后,奶奶大喜,这是她自小熟悉的味道。奶奶娘家家境优渥,嫁进我家这个“寒门”前,有亲人在南京城里开过金店。想来,老冰糖只是她在无忧无虑岁月中尝过的美食之一罢了。时隔30多年,我还记着奶奶吮吸老冰糖时的惬意,以至于如今只要买冰糖就必以黄色晶体为上品。
关于食物的记忆,是有一把“锁”管着的。
在皖西北小县城,我们探望了年过九旬的二大爷。此前,护工向身在南京的我们传递的消息是,二大爷啥都不想吃了,他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但在堂哥和堂侄女接待我们的晚宴上,面对一盘盘老家风味,二大爷却开了胃口。重要的是,他有日子没有见过我们了。
这让我想起,我在报社实习时,某日病倒在租住的地下室里。房东大娘一天没见我人影,便盛了碗热腾腾的小米粥送来,她说:“就知道你肯定生病了,趁热喝了就好。”一碗米油凝腻的小米粥下肚,我精神了几分,竟想落泪。房东一家待我很好,常邀我一同吃饭,都是寻常菜肴,却吃出了家宴的感觉。告别房东家30多年,我一直对小米粥情有独钟,那是最好吃的食物。
写过“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的东坡先生,至死都把家乡的元修菜视为人间至品。无论是被贬路上苦中作乐的文豪,还是一路跌宕起伏依然努力开拔的你我,在以美食和青天明月对话时,心中涌动的还是对人事美好的执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