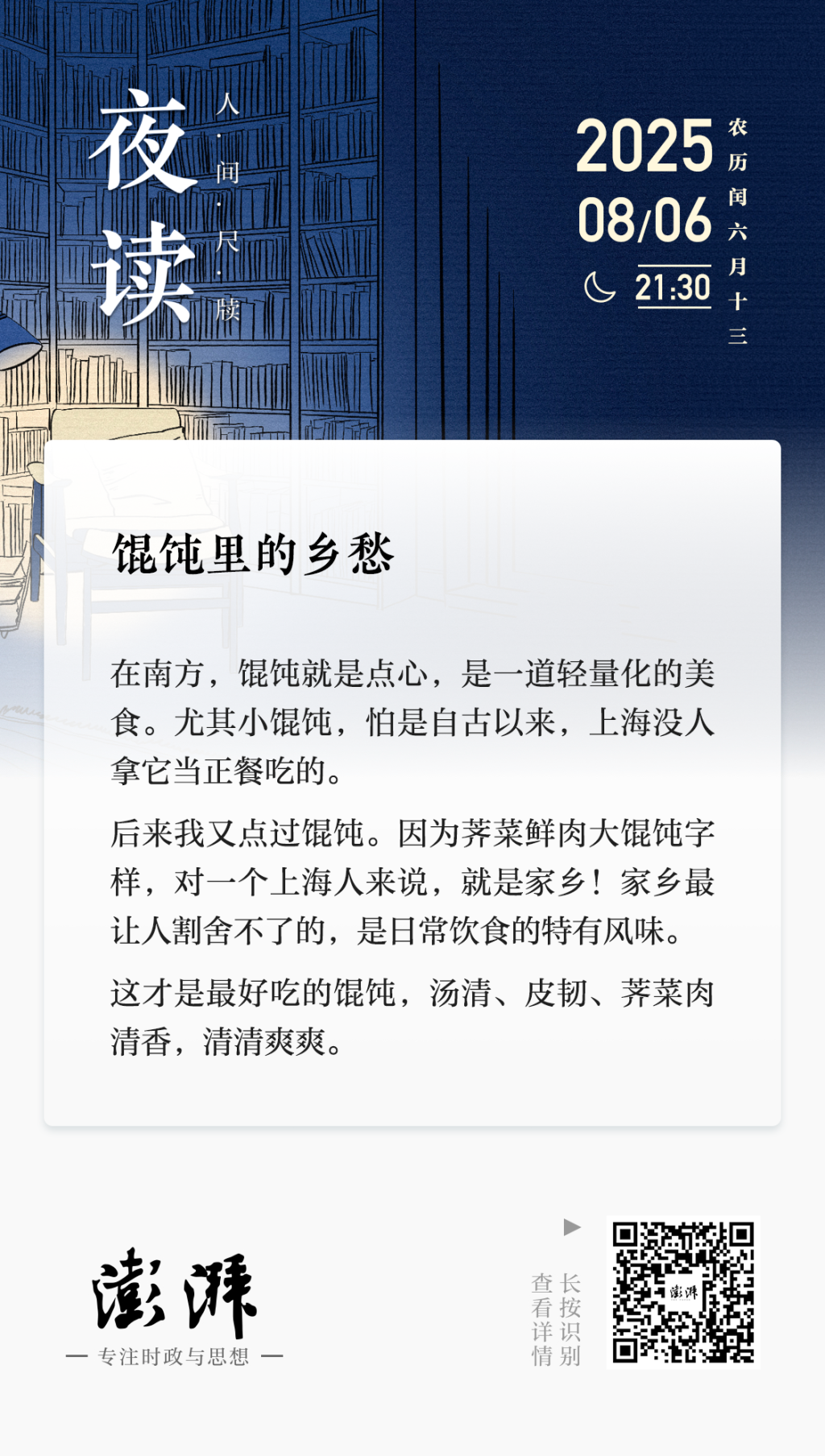夜读丨馄饨里的乡愁
在南方,馄饨就是点心。中餐的碳水世界里,它是一道轻量化的美食。尤其是小馄饨,怕是自古以来,上海没人会拿它当正餐吃的。
但在北京,馄饨好像就是另外一种吃食。我在北京住过几年,小胡同也钻过,通衢大道也转过,但印象中,极少见到专卖馄饨的。街上的小吃,北方传统的有牛肉面、羊肉汤、卤煮火烧,外地的有杭州小笼、重庆小面、云南过桥米线,但馄饨铺子真少。有卖馄饨的,也是某个小吃铺众多吃食水牌里不起眼的配角,挂在边边上,少有食客问津。
不单北京,就我的经历来说,整个北方馄饨都不多。像山西、西安这样的碳水大省,我没见过专卖馄饨的。满街飘着的都是牛羊肉和面食的浓厚香气,对魁梧豪迈的北方人来说,馄饨或许太纤巧,馅不及饺子的丰厚,皮不如包子的筋道,汤头也不似羊杂汤的浓厚,被人冷落,情有可原。
也有例外。北京有家老字号——馄饨侯,招牌就是馄饨,经营至今近八十年,在卤煮火烧堆里以馄饨独树一帜,也是京城厚重历史中的一段传奇。
正宗“馄饨侯”的特点是皮薄、馅细、汤好、佐料全。我特地去吃过,店面就在某段城墙根,门脸并不起眼,虽是老字号,但和周围那些饺子铺、拉面店一样寻常,不见特别。
我倒是喜欢这种朴实无华不丢本分的做派,进店要了一份他们的招牌馄饨,鲜肉馅的,加上大骨汤,汤面满满洒了蛋皮、紫菜,大概还有芫荽。端上来,腾腾的热气里,是黄绿色点缀的一大碗汤馄饨,在北方的寒冬腊月里,看着身上就暖了三分。
不过,真来上一口,老实说,微微失望。肉馅据说选料很讲究,但终究不如饺子馅来得香。而且按照我们南方人的成见,馄饨谁是真吃那肉馅的?那点肉味儿只是点缀,可有可无的。再说那馄饨皮,在汤里一泡就软了。端上来没一分钟,一碗馄饨倒像是面皮汤,可以直接端着往喉咙里灌,难怪他们叫“喝馄饨”。至于“汤好、佐料全”的评语,我也只觉得他家的汤太厚重,大棒骨熬的汤,和馄饨混一起,有点喧宾夺主。
体验过一次后,我再没去过。我瞎琢磨,北京的馄饨味厚重,量也大,估摸着是当主食用的,并不像江南,是拿来当点心,吃着玩儿的。
后来在北京的生涯里,我又在一个不知名小店里点过馄饨。因为水牌上挂着荠菜鲜肉大馄饨的字样,对我一个上海人来说,这几个字就是家乡!点了一碗,一尝,大失所望。荠菜混着肉,本是有一种特殊清香的,但北京的荠菜不知是不是和江南的品种不同,亦或是远途运输让它风味尽失,总之这一碗荠菜馄饨完全没有印在我美食基因里的清香。
那一刻,我悟了:“家乡”这个词里,最让人割舍不了的,有九成是日常饮食的特有风味。
我心里江南的馄饨,就是一道小吃点心,不作正餐的。以前上海中等人家的小姐,吃完晚饭打上几圈麻将,看着月色清朗,弄堂里锈迹斑斑的洋铁灯罩下的街灯还亮着,肚子有点饿。可巧,弄堂里传来熟悉的叫卖声,那是挑着馄饨担子的伙计来了。开窗,叫住伙计,差小丫头端着钢盅锅子,下楼来买馄饨。
馄饨担子是一根扁担,加前后两个木箱子。前头的箱子里装着灶头和锅,后头的箱子有抽屉,一层是肉馅和皮,一层搁现包的馄饨。主顾来了,伙计就在莹莹月色下,把馄饨一个个包起来,再一股脑儿下到锅里,只过一下水,就捞起,放在那碗已经冲调好的馄饨汤里。
馄饨汤,不用熬棒骨的荤汤,就是清汤,但要有一块白白的猪油,融在清汤里,漾成一朵朵油花。再加上点青葱,增香还点缀点色彩。小馄饨盛入碗里,汤还是汤,馄饨还是一粒粒的馄饨,看着就清清爽爽。
这碗馄饨,一直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传来传去。只是现在弄堂没有了,伙计也都老了,馄饨担子也不见了,但哪哪都还有馄饨铺,伙计成了老板,担子成了大灶头。
我想,这才是我心里最好吃的馄饨,汤清、皮韧、荠菜肉清香。
它是江南人吃着玩儿的,轻轻盈盈的小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