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期主持人 王鹏凯
转眼间又聊了一年。每逢年底,就到了盘点、总结的时刻。过去一年,我们通过文字、音频、影像等不同形式,试图观察、捕捉当下的文化动态,理解其背后的时代情绪和社会变迁。想借这期聊天室的机会,让我们不再拘束于文学、影视、技术这样的特定领域,更发散、也更具体地聊一聊对过去一年的观察和感受。
为此我准备了三个问题,请大家分别给出自己的回答,它们分别是:
今年让你感到最意外的消息/动态是什么?
今年你觉得对当下生活最具有解释力的文化作品/人物/言论是什么?
今年让你感到最有希望的一个时刻是什么?

01 AI狂飙与世界主义叙事的远去
王鹏凯:我可以预期到AI在技术层面会有很快的进展,但我有点意外的是,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产生了如此剧烈、深刻的影响。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看到的文字、图片或视频是不是AI生成的,特别是最近几个月,Sora生成的视频特别火。而且它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已经在直接影响社会生活,比如我们上次聊到胡彦斌和易梦玲的新闻,我是第一次意识到,现在的辟谣手段可以变成照片是AI合成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验证真伪。我们对于“真实”的把握已经完全被AI给消解了,这让我蛮吃惊的。
这也让我想到,韦氏词典今年的年度词汇是“slop”,意思是指那些AI生成的大量粗制滥造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海量信息生成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信息?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
王百臻:我时常会有一种错觉,仿佛下意识便会觉得DeepSeek是很久以前的产品,但其实翻开日历看,它主要的两款模型,一个是通用大模型V3,去年12月出的;另一个是推理大模型R1,今年1月出的,看到这个时间点之后,我还蛮震惊的。如果从AI的视角来看,今年已经发生过太多事情,而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起点,DeepSeek走入我们的生活好像是一件很“远古”的事,但回首望去,其实只不过隔了12个月而已。这些事发生的太快了,我们很难去判断,当AI所有的可能性被释放出来后,整个社会究竟会发生什么。

DeepSeek的普及对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会有更大的意义,过去ChatGPT的爆火让大家提前领略到“AI热”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但彼时,我们多数人可能仅仅是看客而非真实的参与者。而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内模型的到来或多或少弥补了这一点,它们以开源、免费的方式,一下子把先进的模型给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使得全民都可以深度参与体验这些工具,或使用它们进行创作。举个例子,我今年有关注那些用AI做短片的人,现在很多影展会有专门的AI竞赛单元,这群人真的可以单枪匹马地使用AI,自己写脚本、画分镜、构思整个故事,做出一部完成度很高的影像作品。这种类似“一人团队”的工作方式在过去可能也是无法想象的。
徐鲁青:在有关AI的叙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叙事。以前国家主义是通过文化工业表达出来,比如在《流浪地球》《战狼》或是《哪吒》里面,但是今年我觉得这种国家叙事好像更多体现在科技竞争,在产业里面,它逐渐发展成中美之间的竞争,今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发现即使是在欧洲的认知里,他们对于世界格局的理解也会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世界格局一下变得很两极。
包括最近我去看《疯狂动物城2》,我在看的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好美国,原来我这么久没有看一个在美国场景下发生的美国故事了,但是在此前我好像是浸泡在这种美国制造的全球文化里面,让我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王鹏凯:最近上映的《阿凡达3》也是类似。我觉得可能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脱钩,是世界范围内语境的割裂。《阿凡达3》上映后,很多媒体、个人都在聊,为什么这套在2009年大火的世界主义叙事,今天走不通了,大家的那些共同关切好像破灭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王百臻:对于“共识”破灭这个问题,我联想到的一点是,各国的右翼反而从中得到了一种共识。比方说在德国大选期间,美国的极右翼会去支援德国的极右翼,包括特朗普上台这样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的保守主义群体中也都引起过狂欢。这些群体仿佛分享着某种坚实的共同诉求,但这种诉求本身却更加接近“各自关起门来搞孤立主义”,当这样一种“反全球化”的观念反而变成了全球热销的共识,其实还蛮神奇的。
02 名人离世就像失去一个人生锚点
王鹏凯:我看到大家另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对一些名人的突然离世感到意外,像是大S和方大同。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消息的感受在今年变得越来越强烈?
李欣媛:是不是因为这些名人更多存在于我们90后、00后的童年记忆里?大S去世对我来讲,它更像一个锚,当这个锚点失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少年时代,那个时期已经离我很远了,这会让我感到有些恐慌,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
面对很多人去世,大家的情绪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很尊重,有些很可惜,为什么大S的去世让大家的心情如此复杂?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我觉得是来源于大S这个人,之前我对于大S这个人的理解,可能和其他台偶明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几年,网络媒介对她们家比较妖魔化的处理,经常被搬上营销号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信息是非常混乱的,但是当她去世之后,很多非常真实、琐碎的细节浮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可以认真地去理解这个人。
徐鲁青:我其实对大S没有特别私人的感情,但是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的一个人去世,好像在那个时刻突然达到了一种和解,我们都纪念她,怀念她之前存在的那个时代。这种和解让我印象非常深,这个时候好像所有骂战都不重要了,大S去世了,这个时候我们来怀念一下大S,我们来聊一聊过去看《流星花园》的感受。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会用流行文化来称呼这些台偶电视剧,但是这些流行文化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来说,好像又那么重要。现在大家阅读和输入的东西都慢慢变得分散了,你很难像谈《流星花园》一样去谈任何一个文化产品,可能在30年之后,某个明星去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想念大S一样去想念这个明星?我觉得可能性会小很多。
王鹏凯:或许也跟媒介环境的变化有关。我前阵子听播客《电影巨辩》聊到,社交媒体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动员平台,它很容易营造出一种感觉,即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名人去世新闻就是一个例子,它带来的冲击力会远远超过以前,过去可能张国荣去世才会上头条,让所有人都讨论,但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名人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会推送给你,刚才聊到的群体认同也就随之形成了。
03 在社会中疲于做自己
王鹏凯:你们今年有读到什么特别有解释力的内容吗?对我来说,是年初读到的《疲于做自己》这本书。它是一本关于抑郁症的社会史研究,核心观点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源于自我意识的内在张力,我们一方面被不断地允诺、期许、要求去实现自己的各种愿望和想法,但另一方面,这些愿望很多时候是被压抑的,因为我们缺乏实现它的条件。
我觉得这本书很精准地解释了当代心理,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问题,今年我们也做了“探秘中国心灵”这个专题,我印象很深的是鲁青采访安孟竹的那篇,有提到类似的观点,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其实一直在鼓励所谓的自我实现和自助,通过心理层面的自我疗愈去消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结构性困境,使人进一步投入市场和社会竞争中,她说:“当这个社会再也无法用成功叙事来安抚自我时,人们开始转向对痛苦的书写,寻求一种新的意义系统。”
张钊涵:我在2022年听了王芳老师人格心理学的节目,前段时间还跟着文晴一起去专访了王芳。结束之后我问了王芳老师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心理分析的强调是不是会掩盖一些社会问题,它会不会变成一种治理术?每个人都在用病理学的语言去剖析自己,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动力去想,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不是我们能够去掌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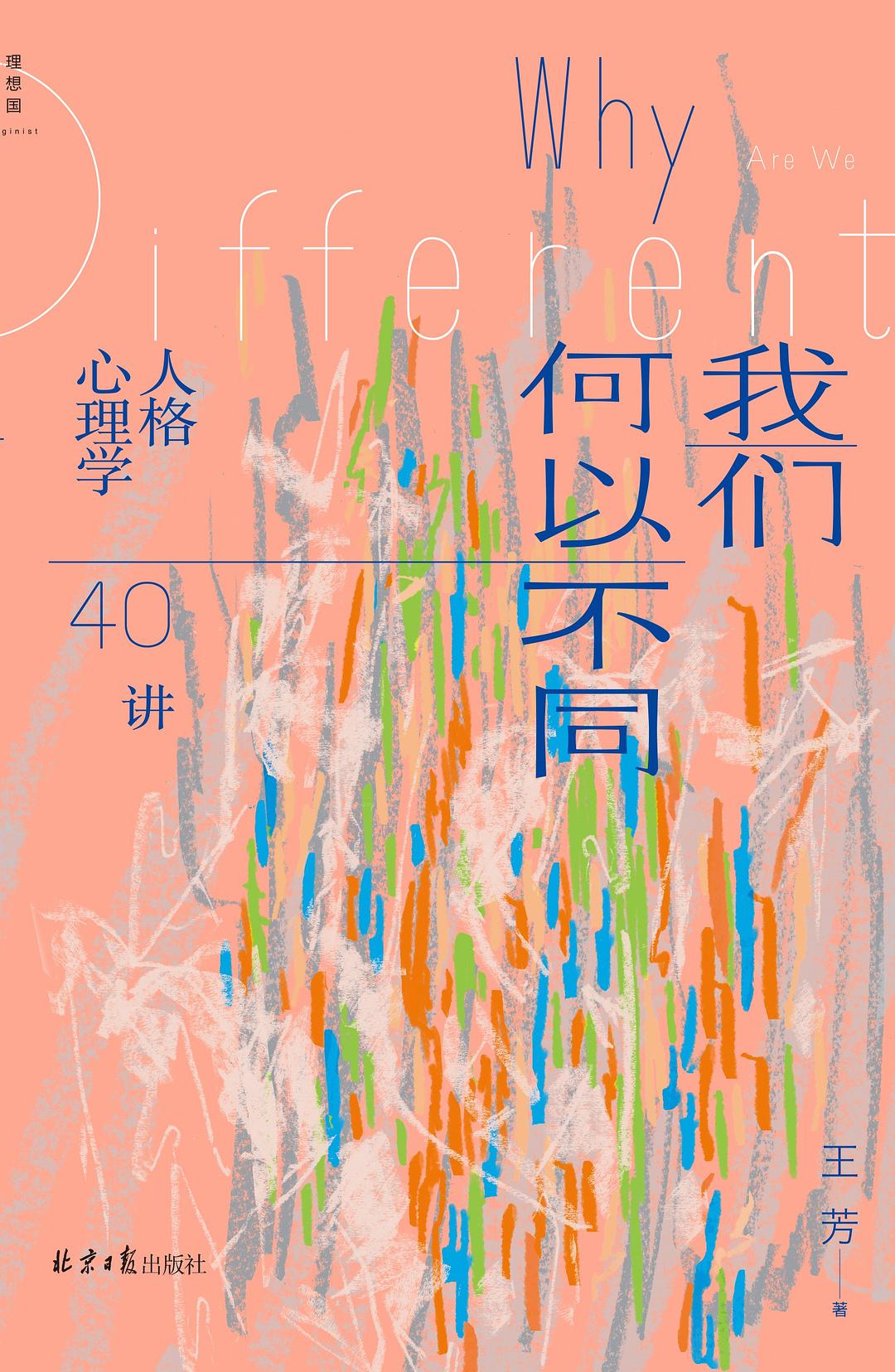
王芳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7
王芳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心理咨询有一个窗口期,就是1到3次,这个时候心理咨询的效果会非常显著,比如一个女生,经过几次心理咨询,她会意识到原来我的生活痛苦,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糟糕的人,而是因为我的伴侣是NPD,这就能给人很强的解释力以及解放感。但进行了8到10次的时候,她又会感觉到心灰意冷:明白这些之后呢,对于现实是不是于事无补的?走出心理咨询室,伴侣还在那里,甚至一些血亲的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很坚决地断掉。现实困境依然存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做这种个人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勾连可能是无效的。
在我说出困境之后,王芳老师讲,面对个人,比如面对面在聊天的时候,她会更加强调,我具体地了解你的困境在哪,给你一些方法上的建议,让你个人走出来,因为光是知道问题在哪,它在社会某个遥远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这是很无力的,只有去行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才会有一些解决的可能性。我听到觉得很感动,也很受教益。
王百臻:我会想到今年诺奖得主拉斯洛的演讲。在关于“人类尊严”这一部分的结尾,他是这样说的:
最终,你随着“历史进步”,突然完全开始相信一无所有;你借由自己发明的设备摧毁了想象力,你只剩短期记忆;你舍弃了对知识、美与道德良善这一高贵而共同的品质。
别动,你还要去火星吗?不,别动,那里的泥沼会把你吞下。
但你的进化之路,是如此壮丽、令人屏息。然而,很不幸,它无法再度重复。
在这个部分当中,拉斯洛用一种非常细腻的方式快速回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当他讲到人类文明到达高峰之后的一个结尾,我们突然看到整个气质快速滑向了一种强烈的悲观。我个人觉得这很符合当下的某种社会情绪,如果单纯从技术或人类文明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已经站在了一个巅峰之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以及科技水平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再往前是什么呢?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对这一问题抱有很深的迷茫和不自信,或者说,对意义的普遍怀疑。
当我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还挺难过的,你好像沿着拉斯洛的视角回顾了一段非常璀璨的人类文明进步之路,然后就到了这里,便戛然而止,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你确实可能抵达火星,但再然后呢?那又会怎么样?这段话是对我今年冲击很大的,我会觉得它对我们当下思考的很多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04 一些感到希望的时刻
王鹏凯:聊到这里感觉有点悲观,我们好像仍处在很多困境当中。这也是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在困境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感到有希望的时刻?
李欣媛:从现在看到的文化产品或人物来讲,说实话我没有感受到太多希望,但人总是需要点希望的,对吧?我决定往回看,看向我的周围,它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我一点希望。从这两年开始,我会更注重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想要跟她们一起,比如玩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会去讨论一些议题,能够感受到单纯的快乐,或者是大家喝酒、交流。这些东西很确定,玩游戏是确定的,你喝的酒是确定的,她在你周围,你可以拥抱她,你可以跟她打打闹闹,这些很确定性的东西会让我从现在的生活中感受到温度。所以说,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刻,目前对我来说是最有希望的时刻。
王鹏凯:我会想到两个时刻,好像都来自对岸。一个是最近朱天文在《岩中花述》的节目,里面讲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很让人难过,但是全部听完,我反而会感到一种激励。朱天文说,如果能穿过任意门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她会拍拍那两个年轻人,告诉他们,你们此后一路去,会拍出非常多值得留下的影片,“你们是值得的。”我特别感动,我会觉得依然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去努力的,即使会遇到各种状况,但就像朱天文那样,侯孝贤病情恶化后没法拍《舒兰河上》,但她还是写完了剧本,想要跟留下的“同袍”们去完成它。
另一个是年中播出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2》,它也是一个观感上很压抑的一个故事,里面讲到很多社会困境,比如杀人犯家人的困境,想要去救助病人的那些心理医生和社工的困境,也包括政客,想要通过政治来改变社会,却又困在政治的泥淖里面。但是看完之后,特别是到结尾,它其实在传递一种希望,人在这些困境里依然努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一句话说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想要去实现的好社会,它不一定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徐鲁青:对我来说可能是尼泊尔Z世代上街的新闻。在世界变得糟糕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会聚在一起,他们在用上一代完全无法想象的政治方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我比较相信一句话,你不要想象先去推翻什么,再建立你想要的世界,你要先建立那个东西,慢慢地其他东西就会被推翻。看到尼泊尔那些00后年轻人,他们怎么用Discord来商议社会问题,在社交网络上去投票,拿海贼王里的海盗旗来做旗帜。其中还借用了像是KPOP里的应援方式,包括去年冬天尹锡悦被弹劾的时候,韩国年轻人们也是拿着荧光棒到街头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创造的新方式,它在坚持去做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

张钊涵:我正在读查建英的《中国波普》,她在前言里写:“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深思熟虑、献身理想的公民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事实上他们是唯一曾经改变了世界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改变世界,那么我愿意相信他们也能改变我们。”我觉得这段话给人的鼓舞在于,有时候身边的某些社会问题会给我们一种坚不可摧的错觉,其实我们收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去动员化的,让你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是原子化的,没有同伴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去妄自菲薄,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可能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并不特殊,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不怎么样的时代而已,往后一定还会潜藏着转机。
王百臻:让我看到希望的是今年11月发生的一件事。德国音乐版权协会(GEMA)针对OpenAI提出了一起版权诉讼,最终取得胜诉。整起案件是关于OpenAI是否侵犯了9首德国歌曲中的歌词版权。判决结束后,德国音乐版权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说了这样一句话,“互联网不是自助服务商店,人类创意服务也不是免费模板。今天,我们开创了一个保护和澄清作者权利的先例:ChatGPT等AI工具的运营者也必须遵守版权法。今天,我们能够成功地捍卫音乐创作者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发生了非常多起创作者和科技公司之间的争端,但大部分案件至今依然处于悬置状态,我们可能下意识会觉得,这种悬置对当事双方而言是一种平等的拖延,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样,AI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着,而科技公司也在不断加码投入资源,这种没有边界约束的高速发展会将对人类创作的使用或攫取变成一种既成的事实。时间并不站在人类创作者这边。这起案件首开了欧洲对于音乐版权侵犯认定的先例,这使我能够看到一点希望,它不再用模棱两可的拖延去搁置问题,而是重申,人类创作者的创作精华是要得到法律保护的,AI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边界的,AI也要遵守法律。这对我们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规避掉很多由技术进步带来的隐患,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