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虚拟爱情以及网络约会平台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讨论网络约会平台,并不是纯粹出于好奇,而是因为互联网再现了柏拉图式的“灵魂-肉体”的双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心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展现肉体的情绪,与现象学模式是不同的,后者展现的是没有理性中介的情绪,是直接从最开始对生活世界敞开的肉体中感知到的情绪。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分别介绍过这两种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一种是相对冷静的柏拉图模式,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再度回到我们的视线;另一种则是现象学模式,它呈现出情绪在肉体中形成和表现的具体过程。
虚拟关系的特点在于它们超越了肉体本身,这使得一些人认为,我们在虚拟关系中能更真实地表达自我。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家黛博拉·卢普顿曾指出:“技术使人类有可能摆脱肉体的束缚……在计算机文化中,我们的身体经常被视为阻碍我们在虚拟互动中获得乐趣的一个因素……在网络文学中,身体常常被称为‘肉身’, 因为它是包裹在心智周围的‘死肉’,而活跃的心智才是‘真正’的自我。”
这样来看,网络技术的发展似乎毫不犹豫地遵循了柏拉图所指出的通往真理的道路。柏拉图曾写道:“我们找到了一条捷径,引导我们和我们的论证得出这么个结论——我们追求的既是真理,那么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掺和在一起,我们的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
毫无疑问,上述两条道路非常相似,仿佛相较于受物质拖累的现实世界,柏拉图早已预见到了虚拟世界的纯净。唯一的(且不容小觑的)差异就是柏拉图所谓“超越肉体”的原因,是肉体感官传递的信息因人而异,甚至对于同一个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变化,肉体感知到的信息也会不同。因此,这些信息难以构成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普世性的智慧。为了达到这一点,根据柏拉图的理论,灵魂要有能力超越肉体的局限,掌握心智构建的抽象模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理念、数字、度量等概念。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由此诞生,在第一部分中,心理学就是通过这种心身二元论对情绪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同样,虚拟技术也忽略了人的肉体,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表现出居住在我们理性部分的“真实自我”。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真理”,而是“爱”。这种爱是通过情绪来表达的,而情绪的根源来自肉体:心跳加速,说话磕磕巴巴,脸颊绯红,目光犹豫,甚至流泪,所有这些反应都表明了肉体在情绪中的参与,尤其是在爱情中的参与。对此,耶路撒冷大学的社会学学者伊娃·伊卢兹提出了她的疑问:“如果互联网彻底抛弃了肉体,或者将肉体置于次要的地位,那么,它又如何能够塑造出情绪呢?更确切地说,技术是如何重新塑造情绪与身体之间的联系的?”在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柏拉图提出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模式,并转向我们在第二部分里谈到的新模式——“肉体向世界打开,为世界所吸引,并与世界展开互动”。
在约会网站上,主体的“自我”必须对自身进行观察和反思,下一个自我定义,由此才能形成对理想伴侣、爱情和生活方式的观点和偏好,进而选择想要约会的对象。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资料”的创建是十分理性的。人们通过心理学的抽象范畴和适当的语言工具将自己客体化,外化自己的主观性,从而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一个公开展示的自我形象。
而这些,正是虚拟爱情与浪漫爱情存在根本不同的原因。具体来说,传统的浪漫爱情并非以“自我认知”为起点,并不会始于一篇“自我展示的文本”。相反,在为虚拟爱情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先是通过自我观察,完成了对自身的客体化,再由语言描述出来。
此外,在浪漫爱情中,吸引力不需要自我觉察,重点在于深入地了解他人。更重要的是,浪漫爱情不会像虚拟爱情那样,将自己视为商品公开展示出来——一旦人们开始公开展示自我,约会平台便会化作买卖爱情的市场。人们必须在自我介绍中突出自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像销售人员在推销他们的产品一样。
伊卢兹称这种现象为“情感资本主义”。在她看来,“这是自我语言与市场资源逐渐融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情绪已经成为可以被衡量、诱导、讨论、谈判、量化和商品化的实体。……认知体系引导着我们去探索灵魂的最深处,它在教会我们情绪的同时,又量化了我们的关系,使我们的关系变得可交换、可替代……并且大刀阔斧地推动了市场规则在个人生活领域的渗透”。
在约会网站上,个人资料之后紧接着就是“照片”。在照片里,我们的肉体以静态图像的形式出现,没有什么动作——但动作才是肉体特有的语言,也是浪漫爱情中吸引力的源泉。此外,用照片展示自己,会促使人们摆出模特的姿势,模仿那些标准化的“美”与标准化的身材,从而抛弃原本自身外貌的特点,反而助长了时尚产业的推广与发展。
当互联网鼓励人们像在市场选购商品一样寻找伴侣,人们出于或多或少的竞争意识,难免开始对照片进行修饰。在供需法则的推动下,人们对自身形象的接受度越低、越不确定,对照片的修饰就越频繁。
因此,在虚拟世界,爱情不仅要求理性化的自我展示,还需要人们借助照片来建构自己的形象,而这恰恰与浪漫爱情的自发性完全相反。浪漫爱情会突如其来地闯入一个人的生活,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或原因,是非理性的,其情感不需要依赖先前的认知。浪漫爱情能够识别出爱人独特的个性,而虚拟爱情则需要大量“可替代的接触者”作为养分,类似于我们对商品的消费。这样的方式最终会让人逐渐远离情感世界。
尽管约会平台上的选择很多,或者说,正因为选择很多,在交换了资料、照片之后,我们最终才会电话交流。通话时,我们的态度会通过说话的语调显现出来——语调是一种区分的信号,可能会激发出感情,也可能让这段虚拟关系走向终结。此外,现实中的见面往往会伴随着失望,因为我们在自我展示时,往往会过于强调甚至只展现出了正面的方面(而这并不符合现实)。同时,内心的欲望与幻想让我们产生出期待,促使我们不断地理想化对方,直到我们真正站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前。顷刻间,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这种失望其实很具有启发性,因为它告诉我们,尽管柏拉图模式在两千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今还借助“强调理性认知”的互联网平台再度回到我们的视线,但柏拉图模式中灵魂所“看”的世界依然忽视了肉体的真实存在。肉体能够通过声音、目光、手势和姿态,展示出“鲜活生动的情绪”,而这些情绪,都是纯粹的理性认知无法理解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什么是情绪”,就不能从柏拉图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出发,也不应当从心智或心理学的角度来描述情绪。相反,我们应当采用现象学的观点,就像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博尔尼亚等人所提出的那样。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来,我们鲜活的肉体从一开始便对世界敞开,这种开放性会立刻唤起“吸引”或“排斥”的情绪,而不需要理性在其间充当媒介。
例如,梅洛-庞蒂曾指出,当你看到一个人时,你所感觉到的远比你对那个人的了解更重要。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与其在网络上浏览那些“自我主观客体化”的个人资料,不如相信亲自见面时的感受更为真实。在现实中,人们走路的方式、握手的力度、就座的姿势、说话的语调、倾听时的目光,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足以引发我们的情绪感受。这些感受往往是个体无意识的产物,但却比所有“有意识交换”的语言信息都更具决定性。因为肉体的表达是不自觉的,在我们浑然不觉之间。它已经向对方传递出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信息。
事实上,我们的肉体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任何照片都无法比拟的。照片只是把我们的身体定格在一个无生命的静止画面中,而现实中的肉体是鲜活的、流动的,它会被周围环境所调动、刺激并吸引,与照片中的形象毫无关系。正如欧文·戈夫曼所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个人生活与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吸引与排斥,总是由“肉体”来承担——这里的“肉体”并非科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身体,而是生活世界中鲜活的肉体本身。
在恋爱过程中,对他人或处境做出快速判断的能力,并不属于那个“权衡利弊的自我”,而属于肉体。肉体的“感觉”能够立刻摸索出最快、最有效的决策,因为它不需要走心智的“长路”。相反,理性想要做出选择,就必须根据自身的需求与期待,为心中的“理想型”列出一张抽象且不切实际的标准清单。而这种肉体之间“即时感知”的能力,或许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擦出火花”,正是“火花”的存在,正是区分出浪漫爱情与互联网虚拟爱情之间质的差别。
毫无疑问,互联网为我们创造了许多以往从未有过的机会,帮助人们建立新的联系。然而,过去的人际关系是由情绪与肉体接触所支撑的,而互联网并不具备这种真实的身体性。浪漫爱情的吸引力往往源自视觉和肢体上的“认同”,而资料栏中的文字与照片反而会干扰感性的判断,削弱浪漫吸引的可能。
这种“认同”往往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因为它不需要被解释或合理化。爱情的降临,本身是一种不讲理的事件。相爱的人必须排除一切理性因素的干扰,才能真正地体验爱情。理智的介入会悄悄剥去爱情神秘的面纱,而那份神秘与魅惑,唯有肉体能够体会,心智却永远无法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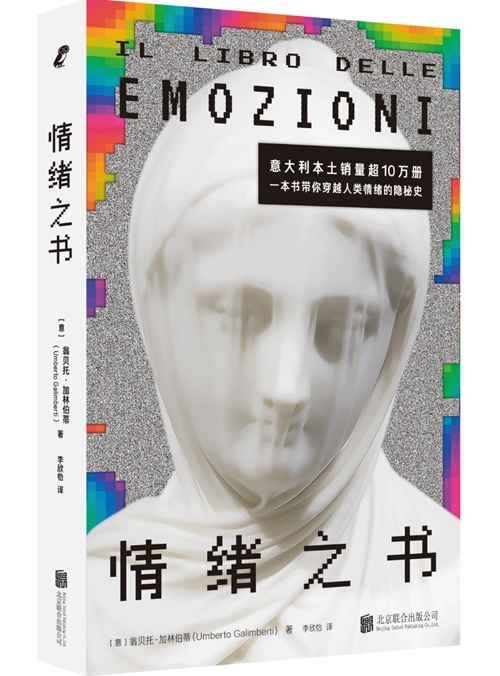
本文摘自《情绪之书》,[意]翁贝托·加林伯蒂著,李欣怡译,新行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